


明蜀王和明蜀王陵
薛登 方全明
成都市龙泉驿区西部黄土陇冈地域,分布着不少朱明皇族成员墓葬,估计不下百座。这些茔圹的规模不尽相同,大墓地宫的内空面积,一般将近二百平米,规模较小者,茔穴内室面积也在三十平方米左右。每座陵圹,无论砖石结构、全石结构,还是砖石琉璃仿木建筑,皆系雕刻精美、装饰华丽、气势宏伟的地下宫殿。这些墓葬,已于1996年11月,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统称“明蜀王陵”。同时,四川省文物局也将其列为全省重点保护的大遗址之一。
一、明蜀王世系及蜀王墓葬的分布范围明蜀王一系,历传亲王十三世。各代亲王诸子,陆续请封郡王而分立支宗者,凡十六系。各系支宗分别传位,以至终明之世,蜀府郡王,总计六十。本文限于篇幅,实难罗列其十六系支宗之六十位郡王的承传世系。故此只列述明蜀亲王之承传世系而已矣。明蜀王首代亲王朱椿,明太祖朱元璋之庶十一子。洪武十一年(1378年)始封,二十三年就藩成都府。蜀王椿之嫡一子悦火兼,既封世子,永乐七年(1409年)先于父薨,赐谥悼庄。永乐二十一年,朱椿薨,赐谥献。永乐二十二年,悼庄世子之嫡一子友土育袭封蜀王。宣德六年薨,赐谥靖。蜀靖王无子,悼庄世子之嫡二子黔江王友土付,已于宣德元年(1426年)薨。以故,宣德七年,竟以悼庄世子之嫡三子罗江王友土熏晋袭蜀王之位,宣德九年薨,赐谥僖。蜀僖王无弟无子,宣德十年,朝廷晋封蜀献王朱椿之庶五子保宁王悦劭火为蜀府亲王,天顺五年(1461年)薨,赐谥和。天顺七年,蜀和王悦劭火之嫡一子友垓袭封,当年薨,赐谥定。天顺八年,蜀定王友垓
A、明蜀僖王陵 B、蜀府罗江王妃赵氏墓 C、石子坡蜀王次妃墓 D、大梁子默江悼怀王陵 E、香花寺献王陵 F、朱家祠蜀府郡王陵 G、七里店蜀府陵墓 H、松树村蜀府王子墓I、十陵村蜀府王子墓 J、青龙五组蜀府陵墓 K、青龙五组蜀南川安靖王陵 L、双林村蜀府内江王长子墓M、来龙村蜀府郡王陵 N、玉石碑惠王陵与继妃墓 O、廖家湾明蜀端王陵 P、明蜀昭王陵 Q、蜀府石泉荣穆王陵 R、蜀府内江庄懿王陵 S、黄连村内江王陵 T、石泉府三座佚名王子墓 U、垮皇坟汶川懿简王陵 V、转龙寺蜀府陵墓 W、蜀府富顺郡主墓 X、定王次妃墓21之嫡一子申钅支袭封,成化七年(1471年)薨,赐谥怀。蜀怀王无嗣,成化八年,朝廷晋封蜀定王之庶三子通江王申凿为蜀府亲王,弘治六年(1493年)薨,赐谥惠。弘治七年,蜀惠王申凿之嫡一子宾瀚袭封,正德三年(1508年)薨,赐谥昭。正德五年,蜀昭王宾瀚之嫡一子让栩袭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薨,赐谥成。嘉靖二十八年,蜀成王让栩之庶三子承火龠袭封,嘉靖三十七年薨,赐谥康。嘉靖四十年,蜀康王承火龠之庶一子宣圻袭封,万历四十年(1612年)薨,赐谥端。万历四十三年,蜀端王宣圻之嫡一子奉铨袭封,当年薨,赐谥恭。万历四十四年,蜀恭王奉铨之嫡一子至澍袭封。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张献忠农民军攻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妃史氏、次妃邱氏(或云原系近侍宫女邱素馨)等,于蜀王府内投井自尽,时明已亡,无谥,明藩蜀府宗系亦绝焉。朱明蜀王,建藩成都。当时的蜀王府,位于成都城内的中心地带,即清代民国所谓的皇城。宅邸范围,包括今四川省展览馆及两边的成都市政府、原省工业厅、市体育中心、实验小学、二十四中一带区域。主体建筑坐
北向南,重重殿宇,层层宫院,四周绕以城垣。并设城门,且建城楼。城墙外围又置护城河濠。蜀王府城的外沿,南(前)面大致及今人民东路———人民西路一线;北(后)面达今之市体育中心及二十四中以北的东御河沿街———西御河沿街一线;东面接近今宾隆街———大有巷内侧往北一线;西面直抵平安桥———马道街外侧一线。恰好是座长宽皆约750米、占地约850亩的方城。护城河濠以外四面,还有广狭不等的附属区域。明蜀王府南城墙中段,设有横排并列的
三道城门,此即王府正门。城门前方的护城河上,置建相应的三座石桥。再往前,则是一片旷坝,横阔与今天府广场相当,纵广比今天府广场还要大出一倍以上,南沿直抵今之红照壁街———新光华街一线。当时在这旷坝广场南端,正对王府城门及城楼,建有一堵巨型照墙,后世俗称“红照壁”。至若蜀府附续建立的十六系支宗,所传六十位郡王,则按朝廷藩制规定,皆不进住封地,而于本藩亲王建邸的府城或州城之内,以及该府州直辖的城郊地区(即所谓府、州的首县境域。比如当时成都府之首县,乃华阳县和成都县。华阳县辖成都东南半城及东南郊二十几乡;成都县辖成都西北半城及西北郊约近十乡)修建郡王府邸而居。关于蜀府郡王及所属支宗成员,及至郡主之类,概不进住封地,而是尽皆建邸居于成都或四郊首县。六十位郡王的子子孙孙,即各等“将军”、“中尉”之类一大帮皇族贵胄,还有女性主、君与其夫婿仪宾,也尽皆邸居成都府城及首县境内,死后照样就近择葬成都四郊和毗邻的州县之地。其中,辈份较低或很低的那一部分宗人,数量过于庞大,而墓葬规模却较卑小简陋,或难列入明蜀王陵范畴。然其上层及中层,也就是历世亲王、郡王,未袭王位而死的世子、长子,还有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以及诸王之妃(结发妻)、继妃(续弦妻)、妾(次妃和夫人)、王子王孙各家的妻妾、郡主、县主之属,总数亦约五百以上。考虑到夫妻合葬之
制(也有一部分因故未合葬),则其陵墓也不少于三百座。这些墓葬的规模,虽然仍有等级之分,但其最小者,盖亦可观。迄今调查发现的这类墓葬,除龙泉驿区二十六座以外,还有成都北郊金牛区天回镇西南凤凰山之蜀悼庄世子朱悦火兼墓及靖王陵。前者已于1970年发掘出土,1980年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至若成都东南郊锦江区琉璃乡潘家沟之蜀王次妃王氏墓(因王氏乃蜀惠王之生母、蜀昭王之祖母,死时,已是昭王在位,故尔按照亲王正妃陵寝的规格和规模置茔园、修造墓圹)、皇明无谥蜀王陵(据考,此乃清代康熙初年由四川地方政府造圹改葬的明藩末代蜀王至澍之墓)及王妃史氏、次妃邱氏墓,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发掘出土。目前所知葬地距成都最远者,为新津县境的庆符恭僖王陵,已于80年代初期发掘。王讳友土票,蜀22和王悦劭火之庶六子、蜀僖友土熏之堂弟也。天顺八年(1466年)始封以建蜀府庆符一系支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薨,赐谥恭僖。下传五世而明亡。总而言之,明蜀诸王及子孙、妻妾和郡、县主的葬地,主要是在成都东郊黄土陇岗区域,尤以龙泉驿区西部较多,估计或有百座以上。但因自然和人为方面的诸多缘故,这些陵墓的寝园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且皆辟为农田,并经多年耕种,竟连碎砖残瓦也难觅见。而其原本高大的坟冢,亦仅残存洪河乡三桥村廖家湾和白鹤村昭王陵两座土堆,余皆夷平为耕种多年的农田。以故,埋在地下的蜀藩陵圹,大多无从稽考。虽经多年调查探访,也只勘得二十三处,凡二十六座。本文拟就既经发掘,且又可供参观的两座王陵和从锦江区琉璃乡迁来我区复建保护的蜀定王次妃墓,给予评介,并作必要的研究。鉴于探讨明蜀王陵寝园规制之需,我们首先将现存本区僖王陵附近那一座未经发掘,但很特殊的茔陵墓主进行探讨。
二、东风渠畔特大茔园墓主考
此墓位于成都东郊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五组境,明蜀僖王陵西1200米左右。墓向290°(东偏北)。当地相传,此处原有一座庙宇,名曰香花寺,以故俗称此墓为香花寺大皇坟。1958年,兴修东风渠时发现,确认是座明蜀王陵。1995夏,成都市考古队与龙泉驿区明蜀王陵博物馆联合调查此墓,并对寝园地面建筑的遗基残迹进行局部勘探和试掘。从而查明其茔地系由三个园子组成,通宽约近150米,前园和中园进深各为97米余,后园通进深192米余,总面积87亩余,约合明制一百亩。联合调查组判之为“成王陵”,正式列入明蜀王陵大遗址保护名单。然按笔者考查,此墓寝园,竟比明制规定的藩府亲王茔域面积大出一倍。而僖王陵、昭王陵的寝园面积,都是大略符合明制规定,未有过度超限。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僖王之侄曾孙、昭王之子的陵地面积,岂得如此超制出轨?所以笔者认为,香花寺大皇坟之墓主,必是一位具有特殊地位的蜀王。且其薨逝及建陵葬时间,只能是在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以前。因为朝廷关于藩府亲王茔域只许占地五十亩(合今43.25亩余),乃系正统十三年明令颁订的一项削藩限藩制度。而明代实行任何一项削藩之制,凡有违规之举,必受严厉惩处。这在有关史籍中,所载实例颇多。尤其是在藩禁法网极端严密峻刻的明代后期,即成王让栩薨逝的嘉靖年间,一贯以循规蹈矩著称的蜀藩,怎会如此明目张胆地犯禁越制出轨?
薨葬于正统十三年以前的明蜀亲王,倒数第一位,乃蜀藩第三世亲王,即僖王友土熏。其茔域面积,亦较后来制颁的五十亩限额大不了多少。再往前推,蜀府第二世亲王———靖王友土育,清嘉庆《四川通志》载其茔陵于成都北郊天山。因此,香花寺大皇坟所葬,非靖王甚明矣。再往前推,也就只有蜀府首代亲王,即蜀献王朱椿了。虽然悼庄世子悦火兼薨葬于献王椿之前十四年,但其既非亲王,墓又早在1970年于成都北郊天回镇西南之凤凰山发掘出土。足见香花寺大皇坟与之无关。所以我们认为东风渠畔这座寝园面积几乎倍于礼法限额的墓主,唯可考虑者,只有蜀府首代亲王,即献王朱椿了。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中期,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江陵市郊发掘出土一座明藩大茔,圹志载其墓主为辽藩首代亲王朱植。《明史·辽王传》载,朱元璋之庶十五子朱植,洪武十一年(1378年),封卫王;二十五年,改封辽王。二十六年,建藩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借口“靖难”,而于燕藩建府之地北平(今北京)兴兵造反。辽王植不肯附依四哥,应朝廷之召,由海路绕道应天(今南京,时为明代都城),朝见侄儿建文皇帝之后,诏徙辽王建藩荆州(今湖北省江陵市),籍已废之湘藩故府而居。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攻入南京,夺得皇位,改元永23乐。辽王植由江陵到南京朝见皇兄,“帝以植初贰于己,嫌之。永乐十年,削其护卫”,仅给辽藩保留“军校厨役三百人”。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辽王植薨,赐谥简(按谥法之`简',意即死者生前狂悖无礼,自高自大,怠慢尊长。此乃所谓恶谥也)。因即荆州城郊,依制定茔域,建造陵圹而葬之。考古发掘探明辽简王寝园占地面积约计80多亩。这与香花寺大皇坟寝园面积很是一致。然而,辽简王朱植既是成祖永乐皇帝嫌恨、排斥和打击的对象,何在茔域反比备受朝廷厚待的蜀藩(据《明史·蜀王传》载,蜀藩历世诸王,多受朝廷表彰和嘉奖),且又葬于正统十三年颁定藩府寝园占地限额制度以前的僖王陵面积大出将近一倍?唯一可通的解释,就是朱元璋曾有特旨,规定其诸子凡封亲王者,死后寝园皆得占地百亩(合今87亩余);而自孙辈以下的一切亲王,茔域面积概予减半。至于正统十三年颁定藩府亲王陵地限额五十亩之制,原因盖在有些藩府安葬太祖孙辈及以下亲王,并不遵守减半占茔的规
定。故尔朝廷只好重新颁诏,以将太祖曾发之口喻,立为一项宗藩必须遵守的制度。若然,寝园占地80多亩(明制百亩)的香花寺大皇坟,必系朱元璋之庶十一子,即蜀藩首代亲王———献王椿之陵地焉。否则,何以解释该墓茔域竟比僖王陵、昭王陵大出将近一倍,却与太祖庶十五子———辽藩首代亲王,即辽简王朱植的寝园占地面积相当。或谓,清嘉庆《四川通志》明确记载蜀献王朱椿之墓,在成都北郊天山。焉得无视志籍而另指一地?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亦曾作过探究。明清所谓的天(音“回”)山,实即今之天回镇西南的凤凰山。1970年,于此发掘出土的悼庄世子墓,地宫内空通进深,竟比僖王陵长6米、比昭王陵长12米,且于中庭建有一座寰殿,这是僖、昭二位亲王之地宫俱无者也。如此规模和规格的地宫,显非世子所应享有。明代宗藩世子的地位,仅只略高于郡王,而在亲王之下远矣。所应享有的地宫规模和规格,绝不可能相当或者超过亲王。故笔者认为,天回镇西南之凤凰山(天山)朱悦火兼墓,原本是为其父朱椿预建的寿寝。不料世子先薨,父必怜而悯焉。鉴于蜀王椿当初在燕藩起兵夺取皇位时,一直态度鲜明站在四哥朱棣一边,所以朱棣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对这位庶弟恩渥有加,多次“赐予倍诸藩”〔1〕。因此,朱椿确有条件请得皇兄特许,以己之墓葬世子。这个作法,并不难于理解。一是父王尚在,岂会先为嗣子择地建墓,而当嗣子猝逝,仓促之间,哪有可能建成凤凰山悼庄世子墓这样一座规模特别宏大、规格又是最高(指与已经发掘出土的所有蜀藩诸陵相较而言)的地下宫殿?二是在父存子殁的境遇中,必然希望早逝之子得以尽快入土为安,怎肯长时厝丧等待新建一座切合世子身份地位的茔圹。基于此种心情,必然促使朱椿以己之寿宫改作嗣子墓寝。故在请得皇兄特例恩准之后,仍按太祖生前旨意———洪武分封的诸藩首代亲王(朱元璋之子),无论贤劣,寝园皆可占地百亩(合今87亩余)的成
例,另行选择在今东风渠畔划定茔域,重新建陵造圹。但是,清代嘉庆《四川通志》缘何记载献王陵于成都北郊天山?笔者按之,天山(天回镇西南之凤凰山)悼庄世子墓,原本既是为朱椿预建之寿宫,后来却改葬了世子。此事自然无须张扬,更不会发表声明;倒有可能严禁有关知情人员内传外泄。因此,民间所知,仍是原先为蜀王椿预建该墓时透出的风闻,以之而成口碑流传下来,致被方志撰著者采访,故尔载误焉。清修《四川通志》于天山(即今凤凰山)仅只载有献王陵和靖王陵,根本未记此地实有的这座悼庄世子墓。通过上述明藩陵葬制度和考古发掘实迹的对照分析。我们认为东风渠畔这座茔域占地面积特大的香花寺大皇坟,应系蜀藩首代亲王朱椿之墓———即明蜀献王陵。
三、明蜀僖王陵
蜀僖王陵位于成都东郊,今龙泉驿区十24陵镇大梁村,墓向130°(西南)。僖王陵地宫,系用厚大的青砖砌建成两列纵连直通的筒拱券,皆作五券五木伏,总1.40米余,拱券外面,又以青砖横砌四道肋墙,分别箍固各段拱券和墓壁蹬墙。后一列拱券通长约22.50米,内空净高6.16米;前一列拱券通长5.70米、内空净高5.60米。拱券前口,原有一道横砌的砖壁(金刚墙)封堵墓门,发掘时拆除。地宫大门前面,两边建八字墙,长近1.5米、通高3.1米余。施单檐硬山式绿色琉璃筒瓦墙帽,龙纹勾头滴水。檐下饰绿色琉璃一斗三升耍头式斗拱。入墓依次为墓门甬殿、甬道、前庭门殿、前庭、中庭门殿、中庭、棺室门殿、棺室。棺室两边设有耳室。甬道内宽5.88米。前庭和中庭内空宽度一致,皆近7米。棺室内宽3.60米;棺室与两边耳室之间的纵隔石墙各厚0.45米;每个耳室净宽1.20米余。
分隔甬道庭室的四座门殿,皆为石结构四柱三开间仿木建筑,单檐庑殿式绿色琉璃筒瓦大屋顶,龙纹勾头滴水,檐下饰绿色琉璃五铺作单抄单昂斗拱。每殿四条石柱,皆呈椭圆形,纵置,长径0.90米,横径0.55米。殿额用整块石板架设于四根石柱之上,长7米(墓门甬殿的石额枋长5.88米)、厚0.60米、宽1.10米。各殿房皆以明间为过道,设门框立颊、门砧门斗、可以开阖的双扇石门。墓门甬殿每扇石门宽1.21米、高2.58米、厚0.16米,阳面各饰九排九行乳钉,并施铺首衔环。其它三殿的门扇,宽厚同于甬殿,高度由前往后依次为2.62米、2.66米、2.95米。阳面皆镌作隔子窗门式样,石刻肘板、横木呈、抹头、腰华、障水。浮雕窗棂,乃由方格与菱格相套,再套以菩提叶片构成十字花纹组合的格眼图案。腰华板浮雕卷草,障水板浮雕莲荷及缠枝牡丹。各道门扇后面,皆有顶门石条,但在墓底石板的相应位置,却未凿有蹬抵顶门石条的臼槽。由于此墓早年被盗,发掘时所见顶门石条,尽被盗墓人推倒一旁,门扇皆虚掩未弥。各座殿屋的次间,皆仿上窗下墙样式。窗棂为阴刻方格与菱格相套,再套以菩提叶片构成十字花纹、扶桑叶片构成圆环花纹组给的格眼图案。这四座殿房的石基,亦为长大巨厚的整块石板,横长约7米(墓门甬殿的石基横长约5.88米)、纵宽约1.10米,埋在墓底平面以下的部分,厚0.60米;露出墓底平面以上的部分,凿作明间门槛和次间地木伏。甬道、前庭和中庭,两边皆建厢房,尽作绿色琉璃筒瓦硬山式大屋顶,勾头滴水仍饰龙纹。檐下或施五铺作单抄单昂斗拱、或饰一斗三升耍头式斗拱。各厢房明间,一律不设门扇,而于阑额下面置欢门,镌刻莲荷、卷草及缠枝牡丹。次间仍作上窗下墙样式,窗棂镌格子门扇形状,格眼、腰华及障水板所镌图案,同于殿门次间,但非浮雕,而是线刻。发掘时,圹志石碑立甬道正中,前置一石雕燔炉,双耳三足,放在须弥式圆坛形云龙纹座子上。甬道两边的厢房檐下及欢门内外,置放数枚将军俑与十数枚兵弁俑。前庭中部,摆放兵马仪仗队和仪卫队俑数百件,排列有序,阵容严整。两边厢房檐下及欢门内外,则置属官文吏、书生方士、夫役仆从、兵弁卫士之类偶人。中庭两边厢房内外,陈列椅橱几案、方桌长凳、车轿步辇等冥器模型,还有太监宦官、女官女史、宫娥侍婢、男女乐伎、供奉执事、近卫随从、僧人道士等陶俑。中庭正中之后部,正对殿门,摆放一矩形石雕拜台,其后设一石刻供案。供案后面,安一石雕胡床式宽大宝座,靠背镌云纹二龙戏珠图案,两边有雕花扶手。胡床式宝座后方两边,亦即棺室门殿的次间近前,又各置一石雕供案。棺室两边耳室内,各有一座陶制库房模型,悬山式房盖,前后檐壁和左右山墙未开设门窗,只在前檐壁面以其阴刻线条画出门窗门锁之类图形。此外还有杯盘碗盏、壶瓶盆罐、盒碟柜椟、箱笼函匣等陶器皿及冥器模型之类随25葬品,皆放在两耳室的石板地面上。棺室正中,为须弥式石雕棺床,通长4米余、宽约2.20米、高0.76米。前端距棺室殿门约1.80米,后端距棺室后墙(琉璃蟠龙影壁)0.33米,两边各留宽约0.70米的走道。棺床前面,置一石雕供案,上放石雕云龙纹香炉,双耳镌作高昂的龙首。棺床之上,为长方形木椁套棺(被盗墓人拆散),外椁长2.80米、宽1.50米,架设在八个石雕云纹椅形抬座之上。棺内尸骨,仰身直肢,头朝墓后蟠龙影壁,此即墓主蜀僖王。棺室顶上施天花,用巨厚石板横铺而成。每块石板厚0.60米以上、宽1米—1.30米不等,长近7米。每块石板,既为棺室的天花,也是棺室两边室顶上的天花。天花距墓底高3.40米。棺室天花正中,浅浮雕一个巨大的八瓣莲花轮,直径3米。每片莲瓣各镌佛教八宝一件,依次分别为鱼、罐、轮、花、螺、盖、月辰、伞,莲心刻日月星云山川乾坤吉祥图语。棺室两边的耳室,是与棺室平行的长方形。前端起于棺室前口的横切线,顺棺室两边石壁往后,纵长2.80米,尽头为封闭的横墙。墙后是与耳室宽度一致(1.20米余)不能进入的夹墙空室,傍棺室两侧回环于棺室后墙即蟠龙影壁背面,其俯视平面呈形。该半回形夹墙空室,填满木炭。耳室之门,设在棺室以内,即棺室两边石墙的前段壁面,作拱形门洞,通高1.76米、宽0.79米,无门扇。此墓甬道及墓室地面,全部铺设石板。地面,由后向前,略有坡降。且于墓内两边接近墓壁墙基一线,自后至前,各设一条浅狭的导流槽,直通八字墙背后埋设的两条排水管。僖王陵的排水管,系用陶瓦筒接逗而成。瓦筒每节长0.27米、后端外径0.14米,前端急收至0.09米,依次接逗,一直埋设到300米以外,低于墓底数十厘米的山冲洼地。由于瓦筒早被泥土的重力压破,或被泥沙堵塞,失去排水作用,致使地宫成为一座巨大的水窖。蜀僖王圹志,置立于高约0.40米的石碑座上。此碑通高1.43米。其中,碑首高0.43米、宽0.78米,矩形,抹角,四缘阴刻云纹花边,额题两边各镌蟠龙图案。额文阴刻篆书4行:“大明/蜀僖/王圹/志”。碑身宽0.73米,仍镌云纹花边。志文阴刻楷书14行,首行标题:“大明蜀僖王圹志”;以左载云:“王讳友土熏,蜀悼庄世子之季嫡子、献王之孙、靖王之/弟也。母妃刘氏。永乐七年二月十九日生,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册封为罗江王,妃赵氏。宣德七年九月/二十日,袭封为蜀王。王淳厚端淑,言动率礼,未尝有/过。尝患风疾,既愈矣。九年复作,遣人驰奏。/上亟命医往视。阅月,复奏疾加。特遣太监昌盛以御医盛/起东驰视,既行而讣音至矣。其薨以是年六月二十/一日,享年二十有六。/上闻讣震悼,辍视朝三日,遣永康侯徐安往祭,赐谥僖。命/有司治丧葬,以宣德十年三月十三日,葬於成都府/华阳县积善乡正觉山之原。呜呼!王为/帝室至亲,早嗣爵位,秉德循礼,宜享福永久。而遽至大故,/非命也耶!谨述其概,纳之圹中,用垂不朽焉。谨志。”僖王陵早年曾被盗,盗洞位于砖券顶部两列筒拱衔接处的正中。但其所盗,无非金银珠宝玉器珍玩之类物品。至于各种冥器模型、石雕器物、陶俑和各种陶瓷器皿等,虽有扰乱和损毁,却未盗取。这些文物出土后,现存成都市博物馆。
四、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
原貌迁建于龙泉驿区十陵镇大梁村的蜀定王次妃墓,原址位于成都东南郊,坐落在锦江区琉璃乡潘家沟狮子山南坡,墓向178°(接近正南)。地宫后面的残冢,现存高度不足3米,底部残径22米左右。1998年夏,成都市动工修筑三环路,年底发现此墓。经研究决定进行考古发掘之后,将地宫拆迁到龙泉驿区十陵镇大梁村明蜀僖王陵附近复建保护。这一拆迁复建工程,已于2000年初完成。定王次妃王氏,乃蜀僖王友土熏之堂弟媳(妾)也。而王氏之嫡孙———蜀昭王宾瀚及妃刘氏的合葬墓,则在1991年因修成渝高速公路,由本区洪河镇白26鹤村境拆迁至僖王陵侧复建,次年告竣。蜀定王次妃王氏墓,现坐落在明蜀僖王陵东300米余,当地俗称朱家大梁子的高坡顶部。根据考古发掘和现场调查资料,其原址茔域的布局和地宫结构形制如下:
(1)原址茔域地面布局概况
定王次妃王氏墓寝园,由每边长约62米的三个正方形园子按墓向纵连而成,总长187米左右。四周建以围墙,并有分隔三个园子的横垣。寝园南端墙垣正中,设有大门廊房。三个园子的地面,分别筑成自南而北,一园高于一园的三级平台地势。其中最后一个园子,又自墓门前方12米以远,再筑一台,占据整个后园之大半部。此乃全茔最高的一级地坪,即第四级平台,纵广43米。此墓的墓道、墓门前的八字墙、整个地宫及墓坑,皆埋在这个平台下面。地宫后面的坟冢,则垒
筑在这个地坪上面。定王次妃寝园,总面积18亩左右,合明制二十亩余。此乃因故未能与王合葬而另置茔域安葬的亲王正妃所享规格。按明代宗藩礼制,亲王之结发妻(王妃),一般与本王合圹而葬,继妃及次妃、夫人,则不得与王合葬,而只能“造圹附葬”于王茔附近,或“附葬其旁”
〔2〕;即使因故单独置茔建墓,其寝园的制颁占地面积也仅十亩(合今8.7亩余)。定王次妃的这座寝园面积,何以达到因故单独置茔的亲王正妃占地之额呢?其实,所谓定王次妃原本蜀藩定王朱友垓的一名侍妾,虽生五子,却属庶出。而定王正妃也生一子,名曰申钅支。定王友垓于天顺七年(1463年)袭封蜀王,当年薨。次年,嫡一子申钅支承袭蜀王之位(即怀王)。王氏作为庶母,依然未具次妃名份。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怀王申钅支薨,子又早殁,因而绝嗣。朝廷于成化八年,选封定王侍妾王氏所生之子———通江王申凿为蜀王(即惠王)。成化九年,惠王申凿按制请朝诰命,尊其生母王氏为定王次妃。弘治六年(1493年),惠王薨。次年,定王次妃王氏之嫡孙宾瀚袭封蜀王(即昭王)。同年九月十九日,蜀王昭王之祖母王氏薨,延至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方才入葬。何以王氏死后的厝
丧时间长达两年又三个多月?很可能是因其嫡孙蜀昭王向朝廷申请提高祖母的营葬规格,直到获准享受亲王正妃之茔制,这才遵旨划地置园,造圹入葬。明代丧葬制度,不仅对各个等级人员的茔域占地面积有所规定,而且对坟冢和坟墙的高度、以及坟墙的圈径都有规定。按制,因故单独置茔的亲王正妃,坟冢规格相当于三品大臣,坟高一丈四尺(合今4.354米),坟墙高七尺(合今2.177米),坟墙圈径九丈八尺(合今30.478米)。由于明藩蜀府陵墓的坟冢都不筑于地宫上面,而垒在地宫后面;又因地宫都建在后园的中央部位,墓室门面的中心点,亦即后园的中心点。如此一来,地宫后面那一段园子的纵深长度,往往短于坟墙的圈径。所以蜀府多数陵墓的坟冢后部,都须超出于寝园后端横墙之外,致其寝园后端的俯视平面呈形状。据我们实地勘察和测算,昭王陵原筑坟冢之后部,超出寝园后端横墙以外21米左右;僖王陵原筑坟冢之后部,超出寝园后端横墙以外27米余,东风渠畔献王陵,因其后园通进深长达192米余,故此坟冢全在寝园后端横墙以内。定王次妃墓坟冢,超出寝园后端横墙部分约18米左右。定王次妃墓地宫上面,既不垒筑坟冢,是必筑有浅土台基,且建房廊,用以遮蔽和保护地宫及墓坑。这种墓葬格局,古亦有之。明代以前,称此房屋为“上宫”;明代则应叫作“明(冥)楼”,据说是作墓主魂灵生活起居之用。考古发掘之前,次妃地宫上面的覆土已被筑路机具铲尽,故未发现原建房屋遗迹。关于明藩蜀府陵墓地宫上面是否建房作明楼的问题,我们将在昭王陵文中详加考论。前面说过,定王次妃墓自地宫前方12米以远,即由墓道往北的后园地面,乃是整个寝园的最高一级平台,也就是第四级平台。其南有纵广19米的一段地坪,是为此墓寝园第27三级平台,低于第四级平台约近2米。据我们对蜀藩几座已知的亲王陵地发掘勘探所获资料,都在这级次高地坪范围内筑有一片石板铺成的旷场,制称石供坝或五供坝。且于供坝正中偏前或偏后部位,建有一座殿屋,所谓享堂。然而定王次妃墓的这级地坪,却未发现供坝和享堂建筑遗迹。甚至整个茔域范围内,也未找见享堂之遗基残痕。原因盖在明代礼制规定,单独置茔安葬的王妃,视同继妃附葬墓,不得单独置建享堂。其魂灵神主牌位,须与本王“同一享堂”
〔3〕供奉。然则明蜀定王之陵,是否就在次妃王氏茔域外不远处呢?有待查考。定王次妃墓园第三级地坪的前部和第二级地坪的后部,发掘出土一片建筑物的遗基。其北沿始于墓门前方26米处,往南迄于后园与中园的分隔横线以南数米。遗基的纵向中线,跟寝园南北走向的中轴线叠合一致,东西两面对称布局。遗基后部纵广5米左右在后园前部即第三级地坪内,前部纵广数米在中园后部即第二级地坪范围内,但遗基东西两面现存缓坡地势来看,寝园第三级地坪与第
二级地坪之间的原筑台坎并不很高,至多不过0.60米。整片遗基,与第三级地坪一致,高于中园地坪0.60米。据这片建筑遗基的特定位置,参以明藩陵墓地面建筑的一般规制和格局,似可判定其为明陵所谓之大宫门(又称红门)及周围一带附属设施的基址。明陵寝园以内的大宫门,乃系一座城楼式门庭通道。一般是在城楼下面正中部位,在寝园中轴线上开设一个城门洞,也有少数为并列的三个城门洞。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发掘出土的大宫门遗基看,显然只有一个门洞通道。大宫门遗基以南,是一片红砂石板铺设的矩形地坪,规整坦荡,南北纵广8米许。而其东西两端的石板多已无存,故难测量出这片石板地坪的原筑宽度。但它以寝园中轴线为准,往东西两面对称铺设的的迹象却很明显。这片石板旷坝,筑于大宫门正前方,犹如当时蜀王府南面大门前方所筑广场一样。明蜀王府广场南沿建有一照墙(红照壁),在定王次妃墓大宫门前方旷坝南沿,也发掘出一堵横墙遗基,用红砂石条砌筑,东西横长20.70米,南北纵宽(厚)1.15米。其中心点恰好正对大宫门,应是一堵照壁的墙基。可知,定王次妃墓大宫门城楼前面的石板旷坝,及其南沿横墙,乃仿蜀王府广场与照墙的格局。定王次妃墓的照墙南面,是一片保持自然原貌的生土芜地。当考古发掘揭去耕土层之后,便坦露出这片俯视平面略呈凸字形、未经人工铲填的生土地段。沿照壁南面墙根的凸字底线,东西横长,盖不小于24米,超过照壁的东西两端各约1.60米以上,自照壁墙根往南,至凸字形的前端,纵长约计12米余。再往南,则是陵墓寝园以内神道的北端起始地带。而在神道的起始一端,与生土芜地的交接界线却是模糊一片。盖因神道由南往北至此而分作两条路径,从横亘于前方的照墙左右两端1.60米以外,与大宫门前面的石板广场相通。这片生土芜地,便位于神道以北、照墙以南及其左右两条分径之间。陵墓神道,依寝园南北走向的中轴线而筑,仅存依稀可辨的断续残迹。在神道北段的东西两侧(茔地的中园,即第二级地坪的前半部),发掘出土一片红砂石条砌筑的基础框格,内铺红砂石板。这些残基上面的耕土中,
夹杂大量的琉璃筒瓦、板瓦、勾头、滴水、仙人、脊兽之类建筑物残片。可见沿着这段神道的外侧两面,建有一系列房廊屋舍,或标志性的建筑物。神道乃以土筑,上面是否铺设石板,因无实物可证,不便臆断。发掘时测量宽度,约13米左右。然按明藩陵墓神道的制颁宽度,限为三丈,合今9.33米。盖因垒筑神道的泥土坍往两边而致增宽之故。神道自北往南延伸97米左右,其前端一带泥土中,又出现琉璃筒瓦勾头滴水、各式鸱吻、仙人脊兽、以及阑额和墙面的装饰物,还有砖石之类残块碎片。可见此处乃寝园大门所在位置,当初这里应有一座大门殿屋和八字墙。然而神道并28未止于此,其依稀可辨的形迹,自寝园大门以
外往南延伸,直到前端农田一带,出土有石灰残渣、砖石碎块、筒瓦板瓦碎片及少许琉璃残块。据当地农民说,这里早年还散落着一些小型瑞兽之类残块。我们推测,此乃牌楼之类建筑物上的饰件。关于蜀藩陵墓出寝园大门以外神道前端置有牌楼,这在1995年调查东风渠畔献王陵时,当地农民就讲到他们先辈曾见那里有座石坊,虽然早被捣毁,但其断残的石雕屋顶、房脊、额枋、石柱等构件,仍埋在该陵寝园神道前端左侧的田土下面。
《成都文物》1999年第4期《明蜀定王次妃墓发掘记》称其陵园东西宽60米、南北长250米。关于陵园的东西宽度,发掘记与笔者测算的结果近似,而南北纵长,却较笔者多出63米左右。原因盖在发掘记将延伸出寝园大门以外那段48米左右的神道,视作寝园的纵长范围,同时又将此墓地宫后面的坟冢北端,当作寝墙之后限。如此自北至南测量的结果,便比陵墓寝园的实际长度多了63米左右。
(2)墓坑墓道和地宫
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原址,其地宫墓坑,南北纵长19.80米、东西横宽11.40米,南端与墓道对接。墓道之俯视平面呈凸字形,跟地宫相接的一端,为凸字形的宽面,开口横阔8.50米、纵广5米余。以南一段的开口面宽3.35米、纵长3.90米。在墓坑和墓道衔接处的西壁,挖有一条斜坡巷道,自墓坑西壁以西十数米外的地面开始,向东往下斜掘,直到墓坑底部。这条与墓向垂直的巷道底面,即由坑底通至地面的走道,斜坡全长约20米、宽4.40米。显系挖坑运土和修建地宫运料之通道设施。地宫建在墓坑之内,系用青砖砌成两列纵连直通的筒拱券,皆作五券五木伏,总厚1.40米。券顶下面两边的蹬墙(墓壁直墙)及后端封口横墙,皆作内外两层,内层为青石砌建,外层用红砂石条砌筑。两边蹬墙(墓壁)各厚1.62米以上;拱券后端的封口横墙厚近2米。前面一列筒拱券,进深7.22米,内空通高3.58米,两边墓壁内空间距3.12米。后面一列筒拱券,进深9.57米,内空通高3.86米,两边墓壁内空间距3.68米。墓室前口正对墓道。墓道由地宫大门前方12米远的地面开始,向地宫大门逐级而下,直到距地宫大门3米余为止。地宫大门与墓道最低一级之间,为一段纵长3米余的地坪,略低于墓室底面。发掘时,这片小地坪几乎被封堵墓门的金刚墙体占据。此墙系以不同材料砌作纵深三层,总厚2.60米。最里面一层,是用青砖紧贴关闭严弥的墓门门扇,砌满整个门框。中间一层,则用五块巨大的青石板垒叠而成。每块石板,紧贴封堵墓门的砖壁和拱券,由下至上,依次横放。最下面的一块石板,横长3.36米、纵阔1.44米。以上石板,长、宽约略递减,最上面的石板横长减至3米、纵阔减至1.35米。五块石板相叠的总高为4.24米。这道青石墙体的封堵面,大于此墓筒拱券的前口。青石厚壁外面,又以红砂石条砌成一道横墙,高、宽皆略小于青石墙面、纵广(墙厚)0.90米左右。拆除封门金刚墙,就展现出了墓门前的八字墙。两墙对称,皆以石雕构件镶砌而成。下置石雕基座,基座以上的墙面两边各浮雕一条立柱。壁阳正中,镌一海棠形框龛,龛内浮雕灵芝卷云图案。墙体以上,是石雕庑殿式筒瓦勾头滴水房面,屋脊之上,顺施莲华眉盖梁额(其断面呈 形,额阳通镌一排仰式莲瓣)。自眉盖至石基底脚,通高2.38米,墙基座宽1.41米。入墓依次为墓门前殿、前庭、中庭门殿、中庭、甬道门殿、甬道、棺室门殿、棺室。每座门殿,皆为石雕仿木建筑结构。檐下正中设门作通道,皆可以开阖的双扇石门。每扇石门的阳面,各镌凿九排九行八十一颗乳钉。各座殿屋的两扇石门,均衡对称。不同殿屋的门扇,高、宽、厚不尽相同。各殿石门,单扇高约1.59米—1.74米、宽0.86米—0.91米、厚0.14米—290.16米。门槛横长1.55米—1.59米、纵广0.24米左右、高0.05米—0.17米。各殿门两边,皆置粗壮的石柱和素面石壁。门框上方,架设宽大巨厚的青石条以为阑额,两端嵌入墓壁直墙。阑额之上搁置石雕庑殿式筒瓦勾头滴水房面。墓门前殿、中庭门殿和棺室门殿的屋脊上面,未施莲华眉盖梁额。唯第三座殿房,即甬道门殿的屋脊上面,施以莲华眉盖梁额。墓门前殿和中庭门殿,建在前一列筒拱券内,屋脊至墓底通高皆为2.54米。甬道门殿(即入墓的第三座殿房)建在前后两列筒拱券的衔接部位,屋脊上面的莲华眉盖梁额,则横架于后一列拱券以内的最前端。这座殿房,自眉盖至墓底通高2.76米。棺室门殿建在后一列拱券之内,自屋脊至墓底通高2.42米。各座殿房的屋脊或眉盖上面,一律用青砖砌壁封闭,直抵筒拱券顶。各庭室甬道两边,皆建厢房,仍为石刻仿木结构,置于0.62米高的须弥式台基上面。前庭两厢各二间,中庭和棺室两厢各三间,棺室前面的甬道两厢各一间。每间厢房,皆以石条作立柱,同时也是相连厢房之间的象征性分隔墙体。方形立柱(或墙体)顶端,架设石条为阑额。如此一来,每间厢房都被框隔成方形壁龛样式,进深0.25米。龛内正壁,线刻格子窗门图形,门缝正中线刻门锁。厢房阑额之上,仍置石雕筒瓦勾头滴水房面。屋脊上面,一律架设莲华眉盖梁额。前庭和中庭两边厢房的眉盖,为墓中中筒拱起券蹬墙(墓壁直墙)之内壁顶部,砖拱内层的一券一伏,即跨压于两边厢房的莲华眉盖梁额之上。前庭两厢的眉盖至墓底通高2.17米,中庭两厢的眉盖至墓底通高2.10米,中庭地坪高于前庭0.07米。甬道和棺室上面,皆施天花,系用大型青石条铺搭于两厢眉盖上面。甬道天花距墓底高2.46米,棺室天花距墓底高2.27米,甬道地坪低于棺室地坪0.12米,高于中庭0.07米。棺室后端横墙壁面,是为青石砌建的影壁,上沿仍置石刻筒勾头滴水房面,屋脊之上仍施莲华眉盖梁额以承天花石板。甬道和棺室天花的仰视面,分别刻绘一幅双凤朝阳图案。棺室后端影壁正中,凿有一个边长约1米的方形头龛。龛下沿壁面,浮雕一宽大的神案图形,案脚及于壁脚。案上龛内正壁,镌双凤朝阳图案,直径0.88米。龛内四角,镶镌云纹。棺室之内,为石雕须弥式棺床,顺墓向纵长3.53米、横阔1.53米、高0.53米。棺床后沿距影壁0.17米、前端距棺室殿门1.17米、两边距厢房台基0.30米。墓室中庭正中,放置一石雕供案。案板纵广0.76米、横宽1.19米、厚0.10米、左右两端的书卷状筒径高出板面0.08米。案下支架,乃是两块竖立石板,一前一后,板面皆与墓向垂直。立高0.73米、横宽1.15米、纵
厚0.22米,两块石板的间距0.29米,阳面雕刻有花纹图案。陵墓前庭、中庭、甬道、棺室各成单元铺设的石板地坪,不仅前一单元略低于后一单元,而且每级地面又由东北角向西南角微微倾斜,以使墓室渗水尽沿西边厢房台基底脚流向前庭之西南角。在石板地坪及厢房石座下面,设有一条排水涵道,向西横穿墓底,由
寝园西部地下通出寝园,渐转西南方向,一直埋设至远处低于墓底的洼地。这条排水涵道系用石条凿槽,连接成为长沟,长面盖以石板,埋设而成。
(3)出土文物
陵墓早年被盗,盗洞共有两处。其一在砖拱券的前端顶部正中,另一处在封闭墓门的金刚墙前方,盗墓者将棺椁全部拆散,连同墓主骨骸一起拖出墓外丢弃。并盗走一些小巧精致的陶瓷器皿。在发掘此墓时,于穿破金刚墙的盗穴内发现有几件小罐和瓷碗之类随葬品。棺床之上,已空空如也。墓内唯存的一块棺椁木板,也未留在棺室里面,而实弃置于中庭之内。其它随葬物品,也都遭到严重扰乱和移动。30前庭存留随葬物品最多,共计150多件。其中百余件是被丢弃在室内中间地带,另外五、六十件抛置于东西两厢。这些随葬品中,主要是琉璃彩釉兵马仪仗和仪卫俑,还有两件的将军武士俑。此外有男女侍从供奉俑、男女宫官执事俑,以及碗罐盒函之类陶瓷器皿。中庭出土随葬物品90多件,主要是男女侍从供奉俑和太监宫官执事俑,还有一些手执各种乐器的伎乐俑,少许车轿凤辇模型和陶制库房模型。甬道内有侍俑10件,棺室已一物无存。一通大理石圹志碑,碑连座总高1.75米,立于前庭东北角。有人为这是被盗墓者移动的结果,其实不然。那么该碑为何不置立于前庭正中,却安放在东北角落呢?前面说过,此墓各个庭室甬道地面,都是自东北角向西南角倾斜,尽管坡降度很小,但这东北角仍属上首地位,或即圹志安放于此的因由吧。圹志碑下的青石座高0.29米,底面横宽0.86米,纵阔0.39米。碑身下端嵌入碑座的深浅尽寸不详。座上碑面通高1.46米。其中,碑首高0.41米、宽0.81米,呈矩形,圆上角,阳面线刻云纹花边。额题两边各镌丹凤图案,额文阴刻篆书5行:“蜀定/王次/妃王/氏圹/志”。碑身宽0.65米,镌云纹花边。碑文阴刻楷书12行。首行标题:“蜀定王次妃王氏圹志”;以左载曰:“次妃王氏,成都在护卫中所副千户敏之女。成化九年九月二十
日,/束力封蜀定王次妃。弘治七年九月十九日以疾薨,享年五十五岁。子五/人,女二人。讣闻。/上赐祭,命有司营葬如制。/圣慈仁寿太皇太后,/皇太后,/中宫,在京/亲王,/公主,皆遣祭焉。以弘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大庆山之原。呜呼!/妃以柔淑,进侍宗藩,享有荣贵,遽止於于斯也。爰述其概,纳诸幽圹,用垂/不朽云”。
五、昭王陵及蜀藩墓葬茔园规制
明蜀昭王陵,原址在今成都东郊龙泉驿区洪河镇白鹤村与十陵镇千弓村邻界之处。墓向190°(南偏东),地宫后(北)面尚存坟冢,残高5米余,底部残径22米左右。1990年,因成渝高速公路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昭王陵实施考古发掘,并拆迁地宫于僖王陵侧复建保护。昭王陵的考古发掘工作,自1991年3月开始,至6月完成。现对原墓的形制、结构、规模、规格以及寝园的调查、试掘情况略作介绍。
(1)地宫
昭王陵地宫,为砖砌筒拱券,五券五木伏,总厚1.40米。拱券内空进深约22米、净空宽不足6米,两边蹬墙及后墙厚2米左右。拱券外面,也跟僖王陵一样,自前至后横砌四道砖肋,用以箍固各段拱券和蹬墙。地宫墓坑宽近13米,总长(包括地宫前面的八字墙和墓道)41米余。入墓依次为墓门前殿、前庭、中庭门殿、中庭,然后是横排并列的左(东)、右(西)甬道门殿与平行的左、右甬道,同样横排并列的左、右棺室门殿与平行并列的左、右棺室,横排并列的两座后壁殿。各
庭室甬道,两边都有厢房,形似六组四合院。各座殿屋及厢房,全为石结构仿木建筑,石雕筒瓦单檐庑殿式和硬山式大屋顶,勾头滴水或镌龙纹、或镌凤纹、或镌五瓣梅花图案。墓门前殿和中庭门殿,各为一进三开间,面阔约6米,自屋脊至墓底高3.80米。皆以明间作通道,设置可以开阖的双扇石门,每扇门宽有1.10米、高2.40米、厚0.15米。门后备有顶门石条,且于墓底凿有蹬槽。前殿门扇阳面饰乳钉,各为九排九行,并施铺首衔环。中庭门殿阑额,浮雕高天白云龙凤呈祥图纹,双扇石门作隔子窗门式样,镌以肘板、横木呈、抹头、腰华、障水。窗棂亦为浮雕,由方格、菱格与圆环相套,加十字花叶组成的格眼图案。腰华板浮雕云纹,障水板浮雕红日霞光与海涛的组合图案。这两座殿房的次间,皆仿上窗下墙样式,窗棂为阴刻方格与菱格相套,再加十字花叶和圆环花叶组成的格眼图案。该二殿的石基,皆为的整块石板,长近6米、宽0.70米,埋在墓底部分厚0.60米以上,露出墓底部分凿作明间门槛和次间地木伏。31横排并列的左(东)、右(西)甬道门殿和左、右棺室门殿,也是双扇仿木石门,每扇宽0.85米、高1.74米、厚0.14米。这四道殿门,虽也各置顶门石条,却未凿蹬槽。其中,东、西两座甬殿前面,紧贴石门,分别横砌一堵砖壁(金刚墙)封闭甬殿门面。这两座门殿,自阑额以上,架设石雕筒瓦勾头滴水房面、石雕屋脊。屋脊之上,又置石雕莲华眉盖
梁额(其断面呈形,顺屋脊的眉盖额阳镌一排仰式莲花瓣)。眉盖上面及两殿之间石壁以上,全用青砖砌墙封闭,直抵筒拱券的顶部。横排并列的左(东)、右(西)甬道门殿,自莲华眉盖至墓底,通高3.20米。两殿之间的壁面正中,镶竖一条表柱,方形,置于高0.61米的须弥座上。表柱净高1.19米、每边宽0.76米。柱阳上段,雕二龙戏珠图案,直径0.69米,圆面弧鼓外凸,侧视呈形。团图外边四角,镶镌云纹。团图下面的浮雕,系由三 部分组成,从上到下依次为昊天祥云、云带缭
绕的高山深谷、激流涌动的海波。三层图象,互有参差,从而构成一幅乾坤图案。横排并列的左(东)、右(西)棺室门殿和两个棺室的后壁殿,也跟甬道门殿一样,在阑额上面架设石雕筒瓦勾头滴水房面、石雕屋脊,屋脊之上石雕莲华眉盖梁额。这四座殿房,自眉盖至墓底,通高2.60米。各庭室甬道两边厢房,以及两座后窗壁殿,皆构建于高0.61米的须弥式台基上面。前庭和中庭两边厢房的须弥台基陡板石,镌有多种形态的祥云。前庭、中庭及棺室两边厢房,各为三栋。甬道两边厢房和二棺室之后壁殿,各为一栋。每栋面阔三开间。明间不置门扇,仅于阑额下面施欢门,镌刻莲荷、卷草及缠枝牡丹。所有次间壁面,皆镌作隔
扇窗门式样,格眼、腰华及障水板上有阴刻图案。所有厢房及墓后左、右壁殿,于阑额之上架设石雕筒瓦勾头滴水房面、石雕屋脊,屋脊上又施石雕莲华眉盖梁额。自眉盖至墓底,高2.60米。前庭和中庭两边厢房的眉盖,即作墓室砖拱起券蹬墙的内壁顶部,筒拱内层的一券一伏,正跨压于两边厢房的莲华眉盖梁额之上。而甬道和棺室两边厢房的眉盖、以及两座棺室后端壁殿的眉盖,则皆作为搭设天花石板的墙梁。两个甬道与两个棺室上面,全部施以天花,系厚60厘米左右的宽大石板横铺而成。天花距墓底高2.60米。前庭、中庭及平行并列的左(东)、右(西)甬道正中,各置一具石雕供案。须弥式案座,系用整块巨石雕凿而成,高0.88米、上下枋宽1.08米、纵阔0.79米。昭王陵地宫,实即昭王与妃的合圹墓。故有横排并列的两座甬道门殿、两个甬道、两座棺室门殿、两个棺室,以及两座后壁殿。其中,左(东)甬道和左棺室两边厢房的须弥台基石,以及后壁殿的须弥台基石,皆饰以浮雕云龙图案,显系置放昭王棂柩之处。右甬道和右棺室两边厢房的须弥台基石,以及后尽壁殿的须弥台基石,皆饰以丹凤朝阳浮雕图案,无疑是王妃安息之所。两个棺室之间,纵隔厢房的壁面下部,镌成一座庑殿式房屋图形,面阔约0.65米、高0.54米。檐下壁面,刻作两扇门扉,呈现略推开之状。因而在棺室之间,形成一条相通的竖缝,表示夫妻二人魂灵便于随时过往相
从。纵隔于左、右棺室之间的厢房,两面廊檐下,摆放有琉璃彩釉太监宫婢侍奉俑。两个棺室之内,各有一座石棺床,纵长3.85米、横宽1.43米、高0.40米。棺床左右两边及后头,留有走道,宽0.33米左右,前端距棺室门殿1.40米。棺床之上,各置一具长方形木椁套棺。蜀昭王圹志石碑,原置立于前庭左后部位,王妃刘氏圹志石碑,则置于前庭右后部位。此墓各庭室甬道地面,全部铺设石板,由后向前,略有坡降。墓底横面,则自中约略隆起而向两边微呈坡降。且于墓室两侧,沿厢房台基,各凿一条导流槽,直通八字墙背后埋设的两条排水涵道。昭王陵排水涵道,跟僖王陵、赵妃墓〔4〕使用陶瓦筒接逗而成的排水32管不同,而跟东风渠畔献王陵等几处蜀府墓葬一样,是用条石凿槽,下仰上覆,扣合连接埋设,直通寝园以外低于墓底的山冲洼地。
(2)墓道
地宫大门外面,仍以砖砌横壁(金刚墙)封堵拱券前口。墓门前面的八字墙,建在两段条石连接雕刻而成的须弥座上。砖砌墙体,仍施单檐庑殿式筒瓦大屋顶墙帽。八字墙高4米余、各长4.20米。八字墙前(南)面是墓道,由10米以外地面开始,向地宫大门逐级而下,直到八字墙基座前端。两道八字墙之间,是铺有河沙与白灰的地坪。另外,在地宫前面的右(西)侧,还筑有一条斜坡墓道,长10余米、宽4.70米,与正面梯级墓道互为垂直走向,达于八字墙之间的墓门前地坪。该斜坡墓道表面,亦铺有河沙与白灰的。为筑这条斜坡墓道,不仅将正面梯级墓道下端挖掉2米多,而且还拆除了右(西)边八字墙的前半段。明显斜坡墓道的挖筑时间,是在地宫、八字墙和梯级墓道建成之后。墓内圹志记载,昭王宾瀚薨于正德三年,葬于正德四年,王妃刘氏薨于正德十六年。可知昭王既葬十二年之后,又掘开墓前圹坑,从右(西)侧挖出一条斜坡墓道,用以入葬王妃。既毕,对于被拆除的西边前半段八字墙和被挖掉的梯级墓道下端,未予修复,即回填完事。
(3)出土文物
发掘过程中,陆续找到夹杂于砖块乱石中的蜀昭王圹志残块,经拼凑辨识,大致可读,碑首与额题、碑座之类,已佚失。碑身阳面,镌云纹花边。碑文阴刻楷 书14行,首行标题:“大明蜀昭王圹志”。以左载曰:“王讳宾瀚,蜀惠王长子也,母妃〔陆氏。成化十六年◆月◆ ◆日〕(按:母妃以下,碑文缺佚十二字。“陆氏”二字,笔者据民国《华阳县志·金石》所录蜀惠王圹志〔5〕,惠王之妃陆氏,因补。生年则按本碑所纪生平推算而得)/嫡生,弘治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册封为蜀世子,七年◆ ◆ ◆〕(所缺十二字,据《蜀惠王圹志》及《明史·诸王世表》补)/月十一日袭封蜀王,正德三〔年◆月◆日以疾薨,享年二十〕(所缺十二字,笔者如上据补)/九岁。妃刘氏,宁川卫前所百〔户、南城兵马指挥明之女。一子,〕所缺十二字,据此墓王妃刘氏圹志补)/赐名让栩,次九哥。… …/上闻讣,辍视朝三日,遗官谕祭,赐谥昭。… …/太皇太后、/皇太后及在京文武衙门皆致祭焉。〔四年十一月◆ ◆ ◆日,择葬〕(所缺十一字,笔者据补)/隆寿山之原。惟/王宗室至亲,享有大国,清心◆ ◆ ,◆ ◆ ◆ ◆ ,◆ ◆ ◆ ◆/◆ ◆ ◆ ◆ ,藩屏有光,考厥素履,宜享多福,年◆ ◆ ◆。/爰述其概,纳诸幽宫,用垂不朽云。/正德己巳十一月二十七日志”。
墓内出土王妃刘氏圹志,须弥式石碑座高0.42米,上下枋横宽0.88米、纵阔0.43米。此碑净高1.36米。其中,碑首高0.45米、宽0.70米,矩形,圆长角,四缘阴刻云纹花边,额题两边,各镌丹凤图案。额文阴刻篆书5行:“大明/蜀昭/王妃/刘氏/圹志”。碑身宽0.60米,镌云纹花边。志文阴刻楷书10行。首行标题:“蜀昭王妃圹志”。以左载曰:“妃刘氏,南城兵马指挥明之女。弘治十年〔◆月◆ ◆日,受册命为〕(所缺九字,笔者据补)/蜀王妃,正德十六年八月初十日以疾薨,〔荣享寿年四十有一岁。〕(所缺九字,笔者补焉)/子一人,曰让栩。讣闻。/上赐祭,命有司营葬如制。/慈寿皇太后、/公皆遣祭焉。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遵制启昭园寿宫合葬。/呜呼!/妃以贤涉,选配王嫔,荣享寿年,贵富兼备。兹◆ ◆ ◆ ◆ ◆ ◆ ◆ ◆。/爰述其概,纳诸幽圹,用垂不朽云”。墓内收集到的各种彩釉琉璃俑、冥器模型、陶瓷器皿等残片碎块,共装90余箱,陆续运入龙泉驿区博物馆。于当年7月开始,进行拼合镶粘,尽力修复。历时4个多月,仅修复160余件———诸如琉璃陶房及箱笼桌案模型、绿釉陶罐、青花瓷碗及杯盘之类、彩釉琉璃兵弃仪仗、仪卫骑俑、胡骑军乐鼓吹俑、马俑、太监宫女琴师鼓乐俑、侍婢什役供奉俑、33近卫随从俑、宫官执事俑、儒生书吏俑、道士俑(应有的僧俑已毁无存)、凤轿模型及轿夫俑(应有的龙辇模型已毁无存),还有一组正在演奏各种乐器的彩釉琉璃乐队俑(已不齐全)。昭王原有的随葬品,远不止我们清理出土的这90余箱陶瓷碎片,而这些碎片的大半已无法拼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明代中后期入葬昭王陵的侍奉俑中,跟明代前期的僖王陵和蜀府悼庄世子墓出土的陶俑一样,都有头戴瓜皮帽的执役俑。原先,人们多以为瓜皮帽兴自满清,而今从多座明蜀王陵出土这种冠式的偶人,足见瓜皮帽应是缘起于明代帝王宫庭某类执役人员的特定冠式,而后传入满州。迨至清人入关主国,因之普及推广,成为全国上下通行的一种便帽。
(4)明蜀王陵寝园概说
明蜀王陵墓的主体和核心,固然系于地宫。但其所属寝园,亦不失为明陵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按《明史·礼志》,“正统十三年定”制(盖系重申太祖之谕):藩府亲王寝园面积五十亩(约合29016.30平方米,即今43.52亩余);藩府郡王,或者包括未继亲王位的世子、世孙,寝园面积三十亩(约合17409.78平方米,即今26.11亩余);藩府郡王诸子(镇国将军)、诸孙(辅国将军),当亦包括未继郡王位的长子、长孙,或者还有因故未能与王合圹安葬的亲王妃,茔园面积二十亩(约合11606.52平方米,即今17.41亩余);郡主、县主,或者包括未能与王合圹的郡王妃、亲王继妃、次妃、夫人等等,茔域面积十亩(约合5803.26平方米,即今8.7亩余)。至若奉国将军及以下三等“中尉”、郡君、县君、乡君之类,寝园面积自当依次递减。我们通过对昭王陵寝园的调查及围墙残基的试掘,勘知其是由两个大致呈正方形的园子,按墓向纵连而成。也就是在长方形寝园中间,筑有一道等分全园的横隔墙。沿围墙和中隔墙残基泥土中,有不少筒瓦碎片和屋脊残块,表明这些墙垣施有大屋顶式墙帽。经测量,昭王陵寝园通长约240米、横阔122米,总面积大致合于明陵礼制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尚未计及地宫后面坟冢超出于寝园后端横墙以外那部分所占面积。事实上,昭王陵原筑地宫后面之坟冢,后部约有21米左右,是在寝园后端横垣以外。僖王陵地宫后面之原筑坟冢,超出于寝园后端横垣以外的部分,则达27米余。昭王陵寝园地面,由前往后,呈一级高于一级的三级平台形势。第一级地坪低于第二级地坪1.70米,从而形成台坎。平分寝园的横隔墙,砌建于这级台坎后面,相距约有14米左右。第二、三级地坪之间的台坎,则在后园的中段偏前部位。上述昭王陵寝园的面积和格局,跟僖王陵近似,却与东风渠畔献王陵不太一致。献王陵系由三个园子组成,通宽约150米,前园和中园,进深各为97米,皆呈矩形,后园却是长方形,通进深192米余。全园地面,由前往后,构成一级高于一级的四级平台。第一、二级地坪之间的台坎在分隔前园和中园的横墙前方,第二、三级地坪之间的台坎在分隔中园和后园的横墙前方,第三、四级地坪之间的台坎则在后园中段偏前部位。具有四级平台地形的献王陵寝园,总面积87亩余,比昭王陵或僖王陵的寝园,将近大出一倍。这在明蜀亲王陵寝中,实乃独一无二的特例。
(5)明蜀王陵神道考释
昭王陵寝园前部,正对地宫前方的中轴线上,尚存纵贯前园的神道形迹,残长百余米、残宽5米左右。神道前端,即寝园大门一带泥土中,夹杂大量的琉璃筒瓦勾头滴水、各式鸱吻仙人脊兽、阑额和墙面的嵌饰物、琉璃斗拱之类残块碎片。足证此处曾建有一座大门殿屋和八字墙。神道后端,与前园地坪台坎之间,有两米多长的一段空缺,表明此处原建有九级石梯踏道。后被当地居民搬走石条,以作它用。至于僖王陵神道,曾改作乡间大路,后又34扩成机耕道,进而拓为砖石混筑的乡村公路,所以故迹已无从勘察。而东风渠畔献王陵之神道,遗迹尚可辨析。其沿陵地中轴线纵贯前园和中园的一段,长180米左右,特别是延伸出寝园大门以外的部分保存颇为完整。这段神道,全长90米、宽约13米(原宽很可能是9.33米,即明制3丈。后因泥土渐往两边坍铺,故尔增宽)、残高0.40米左右(原筑高度可能在0.60米以上,后渐坍低)。当地群众传说,神道前端原有一座四柱三开间的高大石坊(牌楼),早已塌毁,至今左(北)侧田土中,还埋有断残的石枋、额枋和石刻房顶之类牌坊构件。据此推之,昭王陵神道,亦应具有延伸出寝园大门以外的部分,无非长度不及献王陵而已。按献王陵延伸出寝园大门以外的长度,约为园内神道之半。昭王陵神道在寝园以外的长度,可能有50米左右。因当地农民长期耕垦无迹可寻。昭王陵神道的宽度,当亦不止现存的5米左右,而是应为明制3丈,即9米余。因农民扩大耕田,两边铲削,以至于斯。昭王陵神道延伸出寝园大门以外部分的前端,也当如同献王陵那样,原建有一座四柱三开间的牌楼,但已毁失。按制,神道上面,两旁应置石象生翁仲之类。然明蜀王陵墓之石象生一无所存,故尔无从稽考。《明史·礼志》虽载帝陵神道或置“石象生人物十八对,擎天柱四、石望柱二”。又载非皇族“功臣殁后封王”,茔园神道例置“石人四,文武各二;石虎、羊、马、石望柱各二”。爵至公、侯、驸马、伯;官至一品、二品大臣,茔园神道例置“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三品、四品无石人,五品无石虎”,六品以下(全)无。却未载藩府各等级成员陵地应置石象生翁仲的数目。我们只好参照上述《明史》各级官吏和非皇族封爵的各等功臣,以及皇婿(驸马)所享茔园面积,以与藩府各等陵地面积相较,从而类推一个大略眉目。《明史·礼志》记云,非皇族“功臣殁后封王,茔地周围一百步”,大致相当于24180.25平方米,合明制约计41.6亩。“公、侯、驸马、伯及一品官”,“茔地九十步”,大致相当于18586平方米,合明制约计32亩。“二品八十步”,大致相当于15475.36平方米,合明制约计26.64亩。“三品七十步”,大致相当于11848.33平方米,合明制约计20.40亩。四品六十步,大致相当于8704.89平方米,合明制约计14.30亩。“五品五十步”,大致相当于6045.07平方米,合明制约计10.41亩。六品四十步,大致相当于3868.84平方米,合明制约计6.66亩。七品三十步,大致相当于2176.22平方米,合明制约计3.75亩。“七品以下二十步”,大致相当于967.21平方米,合明制约计1.67亩。按前引明制规定的藩府各等级成员陵地面积,亲王寝园远远大于一切高官和非皇族功臣殁后封王所享茔地面积,则其石象生翁仲数目,必也仅“下天子(皇帝)一等”〔6〕,很可能是石人四对,文武各半,或有擎天柱一对,石虎、羊、马、狮、象、望柱各一对。藩府郡王及未袭亲王位的世子、世孙,寝园占地面积与公、侯、驸马、伯及一品官比较相近,则其石象生翁仲数目亦或相同。
藩府未袭郡王位的长子,长孙及郡王诸子孙(镇国将军和辅国将军)、因故未能与王合圹安葬的亲王妃,寝园面积与三品大臣较相近似,则其石象生(按制无翁仲)数目亦应相同。郡主、县主以及因故未能与王合圹的郡王妃,亲王继妃、次妃、夫人等等,茔地面积与五品官员近似,其石象生之置,必也称之。再自奉国将军及以下三等“中尉”、郡君、县君、乡君,茔园面积,递当六品以下,依例不置石象生翁仲等物。由于昭王陵茔地前园及大门以外一带范围,早有数处农家院落,无法进行普探和试掘,只能依据调查和有关史志记载,作出如上考释。除此而外的建筑物、构筑物、陈设物及布局情况,则不得而知。35(6)明蜀王陵茔地后园前半部布局考略昭王陵茔地后园前半部,早在我们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之前已被破坏。据史志所载明代帝王陵寝的一般格局,参以东风渠畔献王陵寝园的调查,至少可以肯定,在昭王茔地前园和后园之间的分隔横墙正中,应有一座城楼式通道建筑,称作“大宫门”或“红门”,一般设为一个拱形门洞,少数置以横排平行并列的三个拱形门洞。献王陵的大宫门城楼,建在分隔中园和后园的横墙正中。经对残基的钻探,查明献王陵大宫门城楼的基址面阔17米左右、通进深将近7米,横排设有三个平行并列的通道。我们估计,在昭王陵或僖王陵茔地前、后园之间的分隔横墙正中,所建大宫门城楼的规模,可能比献王陵小,也许只设一个拱形门洞。在发掘昭王陵地宫的同时,我们也对墓门前方一带进行了考古作业。于筑路工程队驻地北边工棚背后,发掘出一座房屋建筑的台基残迹,周边系用条石砌筑,框内填土夯平,面上铺设小块石板。台基高0.60米、横阔约14米。整个台基的纵广,约在9米以上。这座横阔将近14米、纵广9米以上的房屋基,位于寝园中轴线上,正对墓门前方,相距约有24米许。应是明陵制度所谓的享堂。形的人工土台,似可称作“灵寝台”。另据1995年的一次勘探试掘,发现僖王陵之灵寝台前沿,即第三级地坪的保坎横墙,砌筑于地宫前方22米以远一线。由于在墓门前方14米外,倒塌的灵寝台保坎横墙中,发现有不少琉璃牌楼构件碎城残片,诸如斗拱、鸱吻、仙人脊兽、筒瓦勾头滴水之类。因此,我们估计,在灵寝台上面正中前部,建有一座四柱三开间琉璃筒瓦大屋顶牌楼,或可名之“灵寝坊”。既然昭王灵柩入葬之后,即已填土砌筑灵寝台、建成灵寝坊。那么,迨至十二年后,入葬王妃之时,固不可能拆除灵寝台前沿的条石保坎横墙和台上之灵寝坊牌楼、挖开灵寝台,由正面原筑的梯级墓道入葬王妃刘氏。所以只好从墓前右(西)侧,另行挖筑一条斜坡墓道入葬之。36(7)明蜀王陵茔地后园后半部布局考析昭王陵地宫,构建于茔地后园中央部位,墓室前面的中心点,即后园之中心点(僖王陵及东风渠畔献王陵、蜀定王次妃墓等的地宫位置,亦皆如此)。地宫后面是土冢大坟堆,残高5米余。按明制,藩府亲王陵冢应高二丈五尺,即今7.775米。可见坍蚀多矣。另外,土冢的构筑,须用青砖或条石砌建一圈坟墙,作城垣之状。坟墙高度,也有规定,凡四品大臣以上,乃为本级坟高之半。藩府亲王陵冢坟墙,自城垛至墙脚,通高应为3.88米,即明制一丈二尺五寸。而其坟墙圈径,依制,四品大臣以上,乃为本级坟高的七倍;自五品至七品,五倍;再以下,三倍。因此可知,明藩亲王之坟墙圈径,在54.425米左右。昭王陵冢的坟墙,早已无存;发掘时,残冢底径只余22米左右。显系当地农民长期铲削扩耕所致。明代帝王陵的封土巨冢,制称“宝顶”或“宝城”。北京十三陵各墓的宝城,都是构筑于地宫上面,坟墙圈径多在250米以上,乃至316米。其覆盖广度,远远超出墓坑口的面积。而在这里,据对所有已知蜀府陵墓的采访调查和勘探发掘,证实各墓的宝顶,无一筑于地宫上面,而是一律垒在地宫后面。那么,地宫上面又如何处理呢?发掘过程中,当揭去地宫上面的耕土层和早年人为覆土层之后,在墓坑口两边外侧,发现两行平行纵列的圆形柱洞遗迹。每边一行九个柱洞,对应整齐。墓坑口西边外侧一带,因农民曾经深挖土层、翻筑田埂和开沟排水,致使这行九个柱洞中,有七个遗迹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墓坑口东边上沿外侧的一行九个柱洞,除了最后两个因农民挖土较深而被伤及,其余七个遗迹,则都相当完整。且直径皆在0.49米左右。纵行每个柱洞的中心点间距,分别为2.80米—3.50米不等。每行的第一柱洞,位于墓门横切线前方将近1米,第九柱洞,则在地宫后经墙横延线后方亦近1米。每行第一柱洞的中心点与第九柱洞的中心点,相距24.20米。两行纵列柱洞的横距,将近14米。两行柱洞的外侧,都有与之平行的一条带状石灰浆铺垫层。其厚度,基本是在1—2厘米之间,通宽0.47米—0.55米,内边距柱洞约0.80米左右,且低于柱洞底面约近20厘米。按据上述遗迹,表明昭王陵地宫上面,原本建有一座覆盖面积大于地宫的房屋。所见墓坑口上沿两边外侧的柱洞,应即房屋之檐柱或廊柱留下的痕迹。由于两行柱洞相距将近14米,古代固无如此大跨度的房屋,想必其间还有数行柱子立于地宫顶部。如果所见两行柱洞是为檐柱遗痕,那么地宫顶部就应立有两行内柱。如果所见两行柱洞是为廊柱遗痕,则其地宫顶部就应立有两行檐柱和两行内桩,但因地宫顶部拱券早被拆毁,覆盖的夯土亦皆塌散,上面的柱洞痕迹不不存。至于所见两行柱洞外侧的石灰浆垫层条带,显然就是房檐滴水或散水砖下面铺垫的粘固层。故笔者认为,地宫上面建房为明楼,明楼后面垒土筑坟冢(宝顶),这是明蜀王陵的共通形制和统一格局。
注 释:
〔1〕《明史·蜀王传》
〔2〕〔3〕《明史》卷五十九
〔4〕赵妃墓,位于僖王陵南(偏西)700米余。1978年冬,当地农民开掘水渠发现,并予毁坏。后经成都市文物管理处作为残墓清理,出土一些文物及圹志石碑,现存成都市博物馆。
〔5〕明蜀惠王陵,在昭王陵西(偏北)500米余(昭王乃惠王之子也)。墓圹跟昭王陵一样,于明末被张献忠农民军捣毁。墓内汉白玉圹志碑,可能是被毁墓者误认作宝物扛抬出来,搬运到墓南(偏西)二里许,盖为识者认出,于是弃之。迨至清代,当地居民见其石质如玉,俗呼曰“玉石碑”。民国十三年(1924年),省城古物研究人员访得此碑,因而移于成都通俗教育馆收藏。
〔6〕《明史·诸王列传序言》(作者单位:成都市龙泉驿区博物馆、文化局)
(责任编辑:杨荣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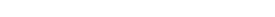
明蜀王陵博物馆 2015 版权所有 蜀ICP备1309412号 网站运营支持:万物智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