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成都的社会经济文化
四川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其最具表现的便是作为中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成都。对于四川,早期的研究比较多,如巴文化、蜀文化、三星堆文化等等;而对晚期的研究则比较少,如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明代四川的状况做一个综合的研究。明代,成都分别是四川布政使司和四川省的首府,又是成都府及成都、华阳两县的治所。明代的成都虽然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川西平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其城市社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繁荣和发展,城市建设也颇有建树,文化、生活习俗方面的川菜、川酒、川茶等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这些都说明了明代的成都在西南甚至整个中国都有重要影响。
1、明代成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1)城市人口的发展状况
明代承元代之蔽,成都人口始终未能恢复到唐代水平,甚至不如两宋时期。从明天顺、嘉靖到隆庆时的编户情况看,成都、华阳两县编户共25—41里。以今成都、温江合并后的市区范围看,明代共计136里,折合14960户[ 陈开俊、戴树英:《马可波罗游记》第四十四章《成都府和沱江》,1981年出版。]。其中,30%的人口集中于成都市区,与两汉时期成都市人口数额相当。据天启《成都府志·赋役志》记载:天顺五年(1461),成都、华阳两县有人丁13219人丁,按每丁6.8人计之[2][ 有关历代中户丁折算人口的研究,李世平先生《四川人口史》有很稳妥的测算方法。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李先生认为,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和万历六年(1578)四川总户数和人口的比例为:1:6.8,1:10,1:12,这里以洪武比例折算。],约为89889人。明后期的人口,据杨慎《药市赋》推测,明嘉靖时期(1522——1566)成都大约有“八万四千人烟”,“人烟”即人户,按每户10人计之[ 这里以李世平先生《四川人口史》142页有关弘治四年(1491)四川总户数和人口数的比例1:10折算。],大约为840000人。这个人口数与明初相比,增长十倍有余,不大可靠。但是,考虑到天顺到嘉靖有百年左右的休养生息期,自然增长率会逐步提高;明初开始时外省向四川大量移民,造成的机械增长较大;成都又是四川经济文化中心、南北商业都会,必然是首当其冲的人口密集区,因此,数十万人口的规模是肯定无疑的。
(2)商品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明代,成都经济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已大大下降,远比不上汉唐之时。明王朝建立后,为了恢复处于衰落状态的四川经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策。明前期和中期,地方官对年久失修的都江堰进行了多次整修加固。为了减轻四川人民的负担,自明初开始,四川都司及行都司各卫所相继建立屯田机构,招募军民参加屯田,在相当长的时期,缓解了四川粮食供应的困难。明政府还制定了奖励农桑的政策,四川到万历时,仅棉花种植面积就达到290000余亩,总耕地面积增加到13400000余亩。人口也因此获得大幅度增长,在明初840000余户的基础上,增加到万历时的262694户[ 清康熙《四川总志》卷十《贡赋》。]。
历代蜀王对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至首代蜀王就藩之前,蜀川已经饱经战火蹂躏,社会千疮百孔。为了恢复和发展四川的社会经济,蜀王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1.对蜀民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2.令有司整修水利,劝课农商;3.对边区住民恩威并施,减免元朝对民族地区的各种苛捐杂税,对向民族地区索取财物的官吏加以重罚;4.严禁官府私下进行财物交易进而损害蜀民利益;5.请求调补南人为匠,以发展蜀川工商业;6.量力拨银,赈灾恤荒;7.发展边贸,监控边境的茶马互市,以茶易马,备军国之用。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的修缮,促进了川中农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减免了一些赋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工商业也得到了发展,蜀人日益殷富。榷场的开设,既可得到军马,传播中原的茶文化,又能增进民族间的情感,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同时历代蜀王还推崇以礼守边。这对于饱受战祸的蜀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幸事。客观上也给予了当地社会一个恢复发展的稳定环境,使得蜀川在明前、中期的两百余年间不为兵革所累,人民安居。
与此同时,成都城市手工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传统蜀锦、金银玉器、蜀纸的生产,比元代有所进步,所谓“俗不愁苦多工匠,绫锦刁缕之物被天下。”[ 《明书·方域志》。]反映了明代成都手工业,尤其是丝绸手工业的繁荣状况。
但是,明代成都官营手工业虽然占据统治地位,民间手工业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传统蜀锦、蜀绣丝织业均趋向衰落,尽管如此,从蜀锦生产看明代四川成都、嘉定、顺庆三大丝织中心中,成都仍居于首位。当时成都市场上有特色的还是工艺美术产品,“蜀锦、蜀扇、蜀杉,古今以为奇产”,蜀锦“名天下”,四川地方当局特设织染局,为宫廷织造精美贡品[《大明会典》卷三。 ]。蜀王府也设“锦纺”,专门督工织造,以供给蜀王府享用[ 清同治《成都县志》卷十六《杂类法·纪余》。]。当时蜀锦织造工艺水平高,所产多为精品,现存于四川省博物馆的两幅明代蜀锦残片,其中有一幅为黄地双狮雪花球露锦,是纬三重纹织物,地为经重平,纬浮花,地呈黄色,花纹为蓝、浅绿、黄、赭等色组成。锦面由大小园镜花纹构成图案,以雪花纹组成球路,小园内织团凤,大园中心是栩栩如生的双狮戏球纹样,纹样内层饰以卷草云纹,空隙处嵌有小园雪花纹。整个锦面层次丰富,浑然一体。蜀扇,这时已能制作折扇,这是明代才从国外传来的技术,而成都工匠已经熟练掌握,所制精美蜀扇,明政府列为贡品。蜀杉木有抬板、双连板等名贵建筑木材,来自岷山千年古木,沿岷江水运出川,享有盛名,蜀地商人用以同苏杭的文绮锦绣、山珍海错等珍贵货物相交换。
印刷业和造纸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程度的复兴,雕版印刷继承了宋代的技艺。蜀献王雅好文学,藩蜀后,“招致天下名刻书傭集成都,故蜀多巧匠。”[ 晋·常據,《华阳国志》卷四十四。]为生产书写印刷用纸,蜀王又于玉女津(今望江楼)旁造纸,取甘泉井水制特等诗笺。其式仿薛涛之法,故其笺亦名薛涛笺,又名此井为薛涛井。[ 四川省文史馆:《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6页。]这时的薛涛笺已用芙蓉皮为料,加入芙蓉花末汁来制作,其色鲜美,越过前代。此外,成都市场上还流通徽纸、迟纸、竹纸,“蜀人爱其轻细,客贩至成都,每卷纸比川戕价贵三倍。”
此外,传统金银器、玉器、漆器、蜀扇、瓷器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精美的工艺品,往往作为贡品。[ 谈迁:《枣林杂俎·川扇》。]
(3)城市商业的发展
明代成都分别为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全国30余个著名工商业都会之一,城市商业繁荣,与省内外贸易往来频繁。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南则巴蜀,成都其会府也。绵、叙、重、夔唇齿相依,利在东南,所以多易所鲜”。[ 张翰:《松窗梦语》卷四。]
成都地区所产蚕丝,已远销东南沿海。《天工开物》卷二记载:“凡倭锻制造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之,丝质来自四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商人不辞万里,运销川丝,贩回胡椒,往来获利。制作精美的薛涛笺贩运四方,成为享誉国内市场的名产。
明代成都手工业发达,一些名贵工艺品,如“缮锦香扇之属”,往往被官府,藩王垄断,“定为常贡”[《明史》卷十二《蜀王椿传》。],因而“名色无多而价甚昂,不可易得”[ 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中。]。一般日用品,如陶瓷、茶叶、生丝、布匹、药材产量不少,流通四方,如成都琉璃厂窑,生产规模很大,占地340余亩,所制青瓷器皿远销省内外。“茶为蜀中郡邑常产”,著名的蒙山茶、峨嵋茶、泸茶、灌县青城山茶、夔门春茶,“初春所采,不减江南”,不少茶叶在成都集散,行销远近[ 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善于营运的山陕商人,已开始进入四川活动。陕商贩运生丝、布帛,在这些领域中“有本自来”。[ 清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十八《食货·盐法》。]
明代成都市区商业比元代繁荣,但未能达到宋代水平。由于宋末元军对成都市区的严重破坏,使明初成都已无法恢复旧貌,只能“因宋元旧城而增修”。自明太祖诏令“筑成都新城”[《明史·李文忠传》。],后成都又经过多次葺修。从天启《成都府志·成都府志图》看,成都市区已具有近代轮廓,城市街道纵横,以蜀王府为中心,街道形成东西和南北走向的若干条大道,再辅以各种坊巷,布局完整、严谨,城内外寺观密布、官衙相望。城市商业兴旺,商品种类繁多。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来看,明代成都的商业具有如下的特点:
1)各类商品的专门市场日益增多,销售范围扩大。为便于各类商品的交易,市区已出现若干经销同类商品的专门销售区域,除唐宋以来经久不衰的花市、蚕市、锦市、扇市、七宝市、药市而外,重要的商品市场还有:皮革市、旧衣市、纱帽市、玉器市、钱纸市、猪市、栏杆市、草市、骡马市、银器市、木市、珠宝市[ 四川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街坊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1—299页。],这些专门市场按商品进货路线或销售渠道自然分布于全城,形成了完整的商业网点,反映了成都城市的供销情况。
2)在经营方面,形成工商结合的格局,许多商号附设手工作坊,以自产自销为主,如栏杆、铜器、金银器、玉器、皮货等商号,自有店铺和作坊,作坊生产加工产品,其后在店铺销售。
3)开拓原料市场,建立较为可靠的原料供应基地,从而使成都商业获得了充分的货源条件。如玉器原料,玉石来自灌县(今都江堰市—本文作者注),俗称土玉,玉行设庄采购,运回成都,以金刚沙解之,琢而为器,富有特色。本市经销的木材,来自松潘、理县,水运来成都,由木商加工销售。其它农副产品均来自成都周围富饶的农村,使成都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
4)作为川西平原,甚至省内外商品集散中心,成都商品来自四方,川西平原的农副产品、川西北高原的牛、羊、马、骡等畜产品,湖北、陕西的棉花,江南地区的特产纷纷运往成都,成都蚕丝、茶叶、金银制品、笺纸、中药材等远销四方,形成范围较广的商品辐射面。
5)成都市区定期集市有了进一步发展,各集市集中交易以某一类富有特色的商品为中心的各类物资商品。如大慈寺为成都历代享有盛名的商业贸易中心,侯溥曾描述它在繁盛时代的风貌:“成都大慈寺,据阛阓之腹,商列贾次,茶炉药榜,篷占筵篿,倡伏杂戏之类,坌集其中。”[ 侯溥:《寿宁院记》。]明代的大慈寺,仍是万商所聚,行医卖卜,市集游乐之处,大慈寺钱红布街,“青楼业也”。[《蜀都碎事》,并见《蜀报》卷五。]
这些商业繁荣的状况,反映了明代成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明代成都的城市建设
明初以后,蜀地社会安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历任封疆大吏对成都城市建设较为重视,续有建树,其中最大的建设是兴修大城和蜀王府。
(1)兴建大城
明代大城称府城,或省会。洪武四年(1371)平蜀后,明太祖派李文忠入蜀安抚,并规划蜀地建设。在此期间,李文忠首先增筑新城,高垒深池,形制略备。[《明史·李文忠传》。]
稍后,都指挥赵清继续完成府城的建设,“因宋元旧城而增修之,包砌砖石,基广二丈五尺,高三丈四尺,复修堤岸以为固。内江之水,环城南而下。外江之水,环城北而东至濯锦桥南而合。”[ 明正德《四川志·城池》。]同时,对府城的城门、月城、敌楼均作了精心规划和施工重建。
洪武二十二年(1389),蓝玉在成都练兵,督修城池。
宣德四年(1428),总兵官左都督陈怀镇压了松叠少数民族反抗后,认为成都是关系全川安定的“根本之地”,又加固城池,并在四门月城各建城隍庙宇一座[ 见天启《成都府志·城郭》并《天启成都府图》。(图附后)]。
崇祯年间(1628—1644),刘汉儒又培修府城一次。
综上所述,明代洪武至崇祯间共修筑大城五次。《蜀中广记·名胜记》认为,明代大城大致恢复到唐宋子城旧貌:“今之东西南北四门,颇为近古。西门者,古之宣化门也。南门者,古之江桥门也。东门者,古之阳城门也。”这种说法,在明代地方志中找不到佐证,天启年间(1621)绘制的《三衢九陌宫室图》,只有大城及蜀王府,与唐宋子城实无关系。由此可以表明,明代修筑的大城,是在废墟上重建的,旧有的子城已被蒙古军彻底破坏,湮没无存。
(2)兴建蜀王府
明代蜀王府的建设,是朱氏皇族在成都建立藩王特权的标志。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封其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由于朱椿年幼和成都残破,虽受封七年之久,但朱椿仅仅是名义上的蜀王,并没有到成都就藩。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见他长大成人,可以离开京城自立了,于是命他暂驻凤阳老家,同时命地方官兴建蜀王府。朱元璋谕旨说:蜀地为西南邦国之首,羌戎等族众望所归,如不兴建雄伟壮丽的王府就不能显示王权的威严。
蜀王府坐落于四川成都府。成都府的历史沿革十分悠久,自禹贡时起已是梁州之地,属古蜀国。其地理位置优越,“上游水陆舟车通荆楚,下吴越达秦魏燕赵。真西南一大都会也。仪城十二里有奇,亦曰锦官城。内列藩封院司府县卫学校祠宇之属,外则含属州邑星棋布列,古所谓天府之国”。[ 明天启《成都府志》卷一。]虽处西南一隅,水陆交通却是便利。据嘉靖《四川通志·舆地志》所载,“大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言地利必资于形势也。蜀国为天府奥区,直坤维而躔井水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形势之险甲于寰宇。按其地东通荆楚,西接吐蕃,南界蛮荒,北连秦陇。其山崒嵂以嵯峨,其水甲渫而扬波。徼道千盘,严关四塞,雄藩巨镇拱卫。’”选此地营建蜀王府当为上上之选。与其他藩王府一样,蜀王府邸的选址运用了中国古代之堪舆学,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古代从春秋时期始就非常注重人与环境的关系。《管子·乘马》有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古人主张城市选址应考虑环境关系,注重将城市主体与周围环境统一经营。帝王的宫苑则大多利用自然山水改造而成,如桂林的明靖江王府建于独秀峰之下,周围众山拱卫,景色优美,确实是一个成功的选择。成都蜀王府的选址则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也。成都府也是一块风水宝地。其境内名山有岷山、峨嵋、青城、巫山,河流有峡江、涪江、嘉陵江、巴江、泸水、大渡河。而“巴城在岷江之北,汉水之南”,[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九《舆地志》。]可谓是“气”之所聚也。城内西北隅有名山武担,明蜀王府就建于武担山之阳。虽不象桂林独秀峰耸立于王府之中,也算得上是背有靠山。有“气”在,有靠山,古人认为如此一来,国祚必久矣!
曹景川侯震奉旨兴工,建设蜀王府。王府基地选择在大城中央,位于成都市五担山之南,显然仍在前代王宫废址之上。明代蜀王府形势森严,府邸周围;环以砖城,周围五里,高三丈九尺;城下蓄水为壕;外设萧墙,周围九里,高一丈五尺,于是形成三道屏障:内城、护城壕和外城。真所谓宫墙万仞,咫尺天涯。嘉靖二十年(1541)又复增修。从其布局来看,与广西桂林市明代靖江王府十分相似。
蜀王府外城萧墙之南有棂星门,门的东面有过门,南临金水河,河上建立金水桥,为三桥九洞通南北,桥南设石兽、石华表各二尊,气势雄伟、壮丽。
蜀王府内部结构复杂、紧凑,廊庑众多,殿阁重叠。据正德《四川志·藩封·蜀府》记载:“太祖高皇帝治定功成,乃封第十一子于蜀,建国成都。洪武十八年(1385)谕曹景川侯震等曰:‘蜀之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壮丽无以示威,汝往钦哉。’震等袛奉,营国五担山之阳,砌城周围九里,高三丈九尺。南为棂星门,门之东有过门,南临金水河,为三桥九洞以度,桥之南设石兽、石表柱各二。红桥翼其两旁。萧墙设四门: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曰端礼,北曰广智。端礼在棂星门之内,其前左右列顺门各二,直房各四。端礼门之内为承运门。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前为东西庑及顺门。承运门内为承运殿;前有左右庑;东西殿左右有东西府;东西偏(屋宇)为斋寝凉殿。后为圜殿。圜殿后有存心殿。又后为宫门,红墙四周,外左、右顺门相向。门内为正宫,鳞次五重。山川坛在萧墙内西南隅。其西为社稷坛,又西为旗纛庙。承奉司在遵义门左。其他长史、仪卫司、典宝、典膳、纪善、典仪、良医、工正、奉祠、审理八所、广备仓库、左护卫俱错居萧墙外。”
此后又增修王府。嘉靖《四川志·藩封·蜀府》载:“嘉靖二十年(1541),奏准包砌以石,设四门如砌城制。端礼门内为承运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前为左右庑及顺门。承运门内为承运殿,前为东西殿庑。左顺门入为东府,前为斋寝,右顺门入为西府,前为凉殿,俱南向。承运殿后为园,殿后为存心殿,又后为王宫门,内为王寝正宫。端礼门前有水横带,甃月池为洞,铺平石其上。东西列直房。其西为山川社稷坛,又西为旗纛庙。东南隅为驾库。东有古菊井,驾路所经。端礼门前外东西道有过门,南临金水河,并设三桥,桥洞各三。桥之南设石狮、石表柱各二,再南平旷中设通道,旁列民居、衙东西者四。正南建忠孝贤良坊,外设石屏,以便往来。更建坊于四衙,东南曰益懋厥德,东北曰永慎终誉,西南曰江汉朝宗,西北曰井参拱极。”萧墙内有菊井,为成都八景之一,曰“菊井秋香”。正德《四川志·成都府·山川》载:“菊井在蜀府萧墙内,即旧府学之前。”康熙《成都府志·山川》载:“菊井,蜀藩萧墙内,成都八景之一,名‘菊井秋香’。”雍正《四川通志·山水》载:“菊井在废蜀萧墙内。”
万历末年,王府毁于火,旋即加以修复。《明史·五行志》载:“万历四十一年(1613)五月壬戌,蜀府灾,门殿为烬。”《明史·曹学佺》:“万历末为四川右参政,按察使,蜀府毁于火,估修资七十万金,学佺以宗藩例却之。”
萧墙南垣在今成都市东西御街一线,东垣在顺城街一线,北垣在羊市街一线,西垣在东城根一线。
经过几次修缮,王府的大体格局已定,规模宏大,足以慑“羌戎”。蜀王府主体为典型的早期亲王府格局,即三宫两殿。以端礼门——承运门——圜殿——存心殿——王宫门——广智门为中轴,两边建筑对称排列,左宗庙,右社稷。在存心殿至承运门间,周廻有庑,同中心承运殿两边的庑构成“日”字形。按《明史》记载,早期的亲王府“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可谓气势辉宏。承运门台基用大青石块砌成,高四尺九寸五分,前后接以云阶、玉陛、石蹬。正殿,即承运殿的殿基也全用平整的大青石块砌成,高六尺九寸,前后也接以云阶、玉陛、石蹬。殿四周围以雕刻图案的石栏杆。殿顶盖青色琉璃瓦。廊房地高二尺五寸,王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后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以上尺寸规格皆为洪武四年即1371年所定)。经过洪武四年(1371)和十一年(1378)两次修订,最终确定亲王府城高二丈九尺,城周为三里二百四十三步三尺,墙基厚二丈,墙顶厚一丈六尺。
王府、萧墙、大城就形成了内、中、外三重城垣,似乎固若金汤,无懈可击。
明大城和蜀王府在明末清初先后遭到灾难性破坏,使这些具有重要历史文物价值的古建筑荡然无存。万历四十一年(1613),蜀王府遭到的那场大火灾,使重要的门坊殿阁全部化为灰烬。万历末,曹学佺奉命调查蜀王府损失情况和修复的可能性,估算修复工程需白银七十万两,大大超出了明王朝对宗藩的财政补贴数额。因此,终明之世,蜀王府没有得到重建。明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于成都,以蜀王府为皇宫,改承运门为承天门,承运殿为承天殿。因蜀王府半为瓦砾废墟,不宜居住,不久,张献忠移居城外中园(今成都市华西坝)。后张献忠放弃成都,撤离时,他命令部下纵火焚烧成都宫室庐舍,夷平城垣垛堞,一时全城火起,公府私宅、楼台亭阁,全部陷入火海。使成都继元末之后再次遭受毁灭性破坏,在这场空前浩劫中,明大城和蜀王府基本上化为尘埃飞灰,成都人口又先后遭受战乱肆虐、杀戮、饥饿,百存一二,基本上处于人烟灭绝状态。
成都自子城在元代湮没后,仅有罗城被作大城。明代建筑蜀王府,俗称皇城。从此,蜀王府为内城,大城为外城。
(3)地方官署的建置
明代蜀王府在大城中心,蜀王之子例封郡王,以县名为王号,王府均建于 成都,如城东南有南川王府、庆符王府,城西有富顺王府、德阳王府、太平王府、内江王府等。除王府外,地方官署的建置如下:
清军都察院。为清军御史官署,在大城东门内正街。清军御史主要职责是监察地方军事。
镇守府。为监察地方官吏而设置的中央派出机构,由太监主持。官署在东门内大街。
巡抚都察院。地方最高官署,景泰四年(1453)建,在按察使前街,即今督察院街。
都指挥使司。官署在东门内正街,洪武四年(1371)置。
总兵府。在都司暑后,相当于今成都市总府街或提督街。
布政使司。官署在城西北隅武担山南麓,武担山包括在内。洪武九年(1376)建。
按察使司。在东门内正街,即今春熙南路。洪武五年(1372)建。
提学道。在清提督学院地址,即今学道街。贡院在府学西,在清尊经书院地址,即今文庙西街之西。
成都府治。在城北,沿宋代之旧。成都县治、华阳县治,分别在府治西东。
成都府学。在城南,即周公礼殿遗址,今为石室中学。永乐年间(1403—1422)重建。
成都县学。在布政使司东,即文圣街。永乐年间(1403—1422)重建。
华阳县学。在县东南,即清大城东南隅。永乐年间(1403—1422)重建。[ 以上官署位置,凡未标明今址者,均以正德《四川志·公蜀》、嘉靖《四川总志·监守》、天启《成都府·学校·成都府志图》所标明的明代街区为准。]
(4)文化、文物胜迹和寺观、园林的建设
明代成都是全省政治文化中心,作为文化古城的胜迹遗址,得到应有的重视,逐步恢复重建。这种重建工作,又与明代文化专制统治的迫切需要结合起来,使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石室书院、成都府学和文庙
西汉文翁石院[ 在今成都文庙前街西段北侧石室中学。]为历代太学府所在地。元代将文翁石室列于学官,设石室书院。明代重视科举,对文翁石室的建设十分重视,在保留前代书院的基础上,又扩建成都府学。文庙祭祀活动也十分兴盛。天启《成都府志·府学图》所绘明代书院、府学、文庙范围十分宽广,南面已抵达南城垣。
2)重建筹边楼
明代在恢复成都名胜古迹时,重建了唐代名胜筹边楼。此楼系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李德裕所建,原址在节度使署侧[ 节度使署在今成都市展览馆东。]。前蜀永平五年(915)失火全焚。南宋淳熙三年(1176),四川制置使范成大重建筹边楼,著名诗人陆游曾作“筹边楼记”[ 见《渭南文集》。],略言唐时筹边楼故基已难稽考,大约在“子城西南隅”。南宋末,成都遭到焚荡,楼也毁灭无存。明代筹边楼已非旧观,曹学佺《蜀中广记·名胜记》“成都府四”说,楼在督察院东。明天启《成都府志·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作镇边楼,绘于督察院东,下莲池附近。
3)杜甫草堂的重修
南宋末年,成都城市为蒙古兵焚毁,位于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幸免于难。至正元年(1341),元朝廷追谥杜甫为文贞。稍后,太监纽璘之孙倾家资在草堂创建少陵书院,元末废弃。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蜀王朱椿在废址重建草堂,其《祭工部文》[ 载《全蜀文艺志》卷五十。]云:“先生距今之世数百年,而成都草堂之名至今日而犹传。予尝纵观万里桥之西浣花溪上,寻草堂故址,黯衰草兮寒烟,是以不能无所感也。于是命工构堂,辟地一廛,匾旧名于上。”草堂建成后,方孝孺特作碑记[ 见同治《成都县志·文艺》。]。此后,草堂又经多次修缮,并得到妥善维护。弘治十三年(1500),经巡抚都御使钟蕃倡议重修,大致形成近代草堂的格局。嘉靖十五年(1546),巡按御使姚礼又加以规划,伺后更筑书院,楹如祠数,左右各翼房廊,引水为槛流,建桥其上以通往来。前门命名浣花深处,包括院后空地,规模宏大。其东则奉佛殿香火,绕以围墙,栽种名花果蔬,再往东辟为水池,引桥下溪水流注池中。至夏日,绿水、莲荷、鱼鸟、古柏交相辉映,有旧时草堂之美。两次扩建,使草堂面积大大扩展,后华阳知县何宇度又摹刻杜甫石像一尊。草堂园林建筑、石刻经过明代扩建充实,已是大具规模,成为成都著名园林名胜。
4)青羊宫的重建
四川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道教宫观建设的历史悠久。青羊宫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宫观之一,《蜀王本记》谓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引《蜀王本纪》。]后人遂以青羊二字为道教寺观之名。东汉末张陵在蜀创天师道,此即道教之雏形。其后天师道流行于蜀地。至唐代尊老子为李氏始祖,令天下诸州皆置道观,诸路各设玄元皇帝庙,并为老子设像,于是成都建立紫极宫[ 封演:《封氏闻记》。]。成都又有玄中观,僖宗入蜀,改为青羊宫。观址初时很狭小,四周尽为菜圃。改为青羊宫后,大兴土木,辉煌壮丽,顿成巨观[《全唐文》卷八十六载僖宗《改玄中观为青羊宫诏》;同书卷八百一十四载乐朋龟《西川青羊宫碑铭》。]。五代和两宋时期,青羊宫成为游览胜地,南宋末毁于战乱。
明蜀王朱椿重建青羊宫,营造亦甚美。何宇度《益部谈资》谓其规模不减两京。正殿内有铜羊,曹学佺说:“有青铜铸成羊,其大如糜。”[《蜀中广记·器物记》。 ]青羊宫同时又是道纪司所在地[ 天启《成都府志》卷三。]。青羊宫因内置青铜铸造的青羊而得名。
5)玉局观的兴建
道教徒谓经有二十四化,其中之一为玉局化。又谓玉局化在成都,老子尝为张陵说《南北斗经》于此[ 彭乘:《修玉局观记》说:“斯化密迩府署(节度使署),制度仅存。自东汉故舆,皇唐崇饰。”载《全蜀艺文志》卷三十八。]。玉局观实建于唐代,前蜀王建拆玉局观,在观址修建五凤楼。前蜀王衍因其旧观,恢复玉局观祠宇[ 位置在今成都柳荫街一带的锦江北岸。]。南宋末祠宇毁于战乱。明代新建玉局观,明人曹学佺于所撰《蜀中广记·名胜记》“成都府三”曰:“《宇寰记》云:‘玉局坛在城北柳堤玉局观内。’按今往新繁路自堤上行十二里有赛云台足以当之。”天启《成都府志·祠庙》:“玉局观,府城北二十里。”二者一自城西北之堤起算,一自城垣起算,里数虽异,方位则同。宋、明人所记皆亲见者,宋人谓在城北。足证宋、明两代各有一玉局观,名同而地异。宋代之玉局观当是在南宋末时成都被毁后明人易地重建之庙。曹引《太平寰宇记》作“城北”非误据讹本即是有意改纂。民国《华阳县志·古迹四》谓后人误据《太平寰宇记》“城北”之说,实则民国《华阳县志》乃误信曹学佺语。如说宋玉局观在城北与苏诗、陆诗均无法吻合。同治《成都县志·寺观》谓“玉局庵……有燔炉一座,铸明成化十九年字”,足见明建玉局观之时间,不晚于此年。玉局观的兴建,也反映了明代成都道教的进一步发展。
6)大慈寺的扩建
至唐代以来,成都一带佛教兴盛,大慈寺就是成都第一大禅院。寺院宏伟壮丽,千拱万栋,数百年间壁画梵王、帝、释、罗汉、天女、帝王将相瑰伟神妙,不可缕数。古市集中蚕市、扇市、七宝市、药市、夜市均包罗其间。香火最盛时,寺庙西抵今锦江街、江南馆街、金玉街、棉花街一带;北至天涯石北街、四圣祠、庆云庵街;东达城垣一线;南至东大街。明代成都僧纲司设大慈寺[ 天启《成都府志》卷三《寺观》。],宣德十年(1435),寺内发生火灾,主要殿宇化为灰烬。到成化十七年(1481),才勉强完成修复工作,但规模大为缩小。明末成都遭毁,此寺也未幸免于难。
7)宝光寺的重建
宝光寺始建于唐代,本名兴福寺,位于城内书院街。明代隆庆四年(1570)重修,寺内有铜铸毗卢佛、庐舍那佛、阿弥陀佛和侍者像各一躯,寺内放有天涯石[ 石至今尚存。]。因寺庙地基狭小,无庭园之胜,又因与新都宝光寺同名,俗称小宝光寺。
3、明代成都的文化教育
(1)川剧艺术
明代成都文化的特点是有“川味”特征的下层群众文化的兴盛,其最高成就是川剧艺术。川剧,是具有鲜明的四川方言特点和音乐特色的戏曲艺术。它是巴蜀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的珍品。
川剧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如果以明代“乐王”陈铎的散曲《朝天子·川戏》和套曲《北耍孩儿·嘲戏七》第一次用文字记载“川戏”演出的状况为证,那么,川剧至少也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从明代开始,戏曲艺术在四川蓬勃发展,川剧中的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大多是明代以来陆续由省外传入,受到四川的语言和民间音乐曲调的同化而嬗变为现今的演唱形势的。
川昆,就是四川昆曲,它源于江苏昆曲,但又有四川的烙印。虽然上演剧目不多,但风格独特鲜明。川昆悠扬婉转,流丽清远,一唱三叹,在川剧声腔中独标一格。
高腔,是川剧中最有特色、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源于江西的弋阳腔。川剧剧目中的大约50%都是高腔戏。高腔的基本特点是“一人唱、众人和”、“帮、打、唱”为徒歌;音乐曲牌丰富,换腔转调灵活;长于叙事抒情,艺术个性很强。
胡琴,包括“西皮”、“二黄”和“阳调”三个组成部分,属板腔体音乐声腔,源于湖北一带之汉剧。“西皮”的特点是轻快活泼、刚劲有力,比较适合表现人物激昂欢快的感情,它正好与“二黄”的典雅、深沉、苍凉和悲壮形成鲜明的对比。而“阳调”则近于“二黄”,但更加沉郁悲愤,适于塑造悲剧形象和烘托悲剧气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弹戏,又叫“川梆子”或“盖板子”。它是用盖板胡琴为重要伴奏乐器进行演唱的一种形式,源于陕西秦腔。从音乐表现上看,弹戏有悲、喜之分,习惯上称为“甜皮”和“苦皮”;弹戏旋律优美、节奏鲜明。正所谓“蜀地亢音与秦近”、“秦腔梆子响亮低”。
灯戏,源于古代巴蜀民间迎神赛会的歌舞表演,唱的多为民歌小调,富有生活气息,很受群众喜爱。
我国戏曲角色行为分类,一般通行“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分类法。川剧与其它剧种大同小异,分为“小生”、“旦角”、“花脸”、“丑角”等类。这既反映了川剧表演艺术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对川剧传统行当分类法的继承。
正所谓“戏无情不动人,戏无理不服人,戏无技不惊人”,戏曲表演不仅要剧情动人,戏理服人,还要技艺惊人。川剧的特技,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动人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的表演风格。主要有:缠水发、变胡须、踢慧眼、变脸;除此之外,还有褶子功、藏刀、大刀走路、上肩耍人、提粑脚、耍蜡烛、贴墙壁等。这些特技,积累了前辈艺人的表演精华和技巧功夫。特技的运用,能渲染舞台气氛,烘托演出效果,外化人物心理活动,在完整的舞台艺术中显得和谐得当,具有惊人的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川剧艺术虽然是四川的地方剧种,但它并不保守。凡是研究过川剧的专家学者们都认为:川剧对于兄弟剧种和其它艺术形式的消化和吸收能力很强,而保留自己剧种的艺术特色和地方风格的能力也较强,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表演体系。
(2)书院及茶馆、书场
明代成都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是书院的兴起。明代成都有子云书院、大益书院、浣花书院等。成都茶馆和书场,素来为人所称道,这是成都群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蜀人饮茶渊源自古,汉王褒《僮约》即有“武阳(今新津)买茶”的记载。晋人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说:“芳茶冠六清”,这些是成都人饮茶习俗的最早记载,它在全国都是最先形成的。饮茶的茶具有盖碗和茶船,据说承碗的茶船是唐代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女所创制,这是成都人特有的饮茶方式。书场是成都城市群众清闲的另一场所,一般书场都兼营茶舍。书场内有评书、扬琴、清音、竹琴、金钱板等各种曲艺表演。其中评书犹为群众喜爱,早在东汉四川说书就很盛行,成都有东汉说书陶俑出土,生动的表现了“负鼓盲翁正作场”的形象。
4、明代成都的生活习俗
四川,其名源于《华阳国志·蜀志》所载“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而其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盖因其自然环境条件好。既有适合于农耕的气候和土壤,又具有丰富的植被和各种物产资源,因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四川饮食馔宴包括川菜、川酒、川茶和四川特色的娱乐文化,在全国享有盛誉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川菜
川菜是中国四大菜系之一,它以“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而名满天下。其特点是:味多、味广、味厚、味浓。其基本味是咸、甜、麻、辣、酸。用这5个基本味调配出的复合味型又达23种之多。川菜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风味独特,深受我国人民群众喜爱,而且在国外也享有较高的声誉。
四川得天独厚,江河纵流,沃野千里,高山峻岭,物产丰富,水源充沛,气候温湿。因此先有李冰父子治都江之堰,后有武侯设屯田之利,秦汉以来,物富民殷,号称天府之国。[ 陶文台:《中国烹饪史略》,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第208—209页。]天府之国的四川,为川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川菜之名在宋代正式见于典籍,许多诗中屡见“蜀味”、“蜀蔬”之赞。川菜进入了宋京汴梁、临安城中,出现了很多专营川菜的酒楼,成为在全国有巨大影响的菜系。宋代记载了北宋汴梁(今开封)“有川饭店,则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 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卷四《食店》。]南宋时陆游曾经居四川,并写下关于川菜的优美诗篇:“剑南山水尽清晖,濯锦江边天下稀。烟柳不遮楼角断,风花时傍马头飞。芼羹笋似稽山美,斫脍鱼如笠泽肥。客报城西有园卖,老夫白首欲忘归。”明代状元杨慎在《升庵外籍·饮食部》中,记录了巴蜀的茶、酒、食品、饮宴资料76条。
四川历史上有“尚滋味”、“好辛香”的食俗。由于气候潮湿,因此川菜有麻辣的特点,以利于发散人体湿气。但川菜绝不仅是麻辣味,而是麻、辣、酸、甜、咸、烫、嫩、鲜诸味皆备,各种味道巧妙搭配,调配出家常、鱼香、麻辣、怪味、椒麻、酸辣、糊辣、红油、咸鲜、蒜泥、姜汁、酱香、麻酱、烟香、荔枝、五香、香糟、糖醋、甜香、陈皮、芥末、椒盐、红烧等几十种味型。长期以来,川菜形成了一种选料严格、刀工精细、烹制讲究、花色品种丰富、味道多又富于变化的风格特点。它不仅适于小炒、小烧的家常风味,而且还以精于山珍海味、传统筵席的大菜的制作而见称于世。川菜绝大多数菜品是荤素兼备,荤而不油,浓而不腻,味重清鲜。就以家常川菜而论,麻辣味仍是少数:像姜汁味、鱼香味、宫保味、糖醋味、怪味等,仍属于多数。所以人们对川菜曾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赞誉。另外,川菜的炒菜不过油、不换锅、一锅成菜的烹制方法,也是很有特色的。
四川小吃,亦风格独特,闻名中外。小吃,按习俗一般多用于早点,打么台(也称打尖儿)、宵夜筵席的配合,也可作为正餐。它的某些品种还是佐酒佳肴。小吃各地都有,惟独川味小吃分量小得出奇、花样多得出奇、制作精得出奇、味道美得出奇。它源于实践,扎根民间,素有选料严谨,制作精细,造型讲究,味别多变和注重色、香、味、型的配合著称,并以蒸点、汤点、酥点为擅长,深得百姓的喜爱。
我们一般所说的川菜是一个大众菜系,比较平民化。但是在上升到蜀王府时,这宴席又是相当豪华和奢侈的。关于蜀王宴席的菜谱内容,主要是由具有巴蜀风味的川菜构成,因为蜀王世居四川,早习惯饮用川味,故而其宴席不乏蜀味或者说四川特味菜;同时四川又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蜀王宴席又吸收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某些佳肴名菜,如羌族的羊肉附片汤、虫草鸭子等。另外明蜀王宴席还必须服从朝廷颁发的各种宴席礼制,别上下尊卑,列如《明史·礼志十》记载:“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与同致仕会,则同序齿。”否则,若是僭越皇帝或国家礼法,轻则要遭到呵斥或惩罚,重则被削爵夺位,甚至处死。
(2)川酒
四川在很早时候就已经酿造美酒了,《华阳国志·蜀志》中曾记载:“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此后扬雄和左思的《蜀都赋》中对蜀酒有大量的文字记载,隋唐诗人对蜀酒也写下了大量诗篇,如杜甫在《戏题寄上汉中王》说“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蜀酒发展到明代的时候,出现了许多有名的酿酒糟房,如“温德丰”、“德盛福”等,川人利用大米、糯米、荞子、高粱、玉米混合酿出天下有名的“杂粮酒”,清代时更名为“五粮液”,在今日更是妇孺皆知的名酒;又如薛涛酒,源于唐薛涛在蜀的故事,“明时蜀王犹取其井水造笺”,[ 清王培苟:《听雨楼随笔》,见袁庭栋著:《巴蜀文化》,第41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此井水清澈甘洌,酿出熏人美酒,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全兴酒。
明代是四川名酒发展的重要阶段。明万历年间(1573—1619)建成了泸州老窖之池,由此奠定了这一“四百年老窖”名酒的基础。我国另一大名酒五粮液产地宜宾,在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酿酒的专业作坊“糟坊”,“温德丰”和“德盛福”就是当时比较有名气的糟坊。绵竹自古以来就有酿酒的传统,唐代就在绵竹酿造出了“剑南之烧春”的名酒,以后在元、明两代连续以造佳酿而闻名蜀中。
四川酿好酒与爱喝酒的习俗紧密相连。一年四季,人们是春种秋收、修房盖屋,或是婚嫁丧葬、做寿请客,都离不开喝酒。除夕之夜,一家人要喝“团年酒”;正月间,亲友会聚要喝“春酒”;栽秧时节,人们喝“栽秧酒”;到夏收、夏种时则喝“开镰酒”、“收镰酒”;到了秋收时节要喝“丰收酒”。此外还有“寿酒”、“婚酒”、“满月酒”等等。
四川人饮酒多讲究慢品、慢饮、细饮,尤其是相聚共饮或个人独酌时,更时徐徐举杯、慢饮细品,边吃边摆龙门阵。下酒菜可丰可俭,或卤肉、麻辣兔丁、凉拌心肺之类,或炒或盐煮花生、黄豆等,都是下酒的佳肴。
总之,名酒的形成和酒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四川酒文化的发展较早也较发达,但是人们对酒文化的认识,是由不自觉到自觉,由饮酒的无度到有度。为了维护不同的社会秩序,进而将饮酒行为与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相联系起来。酒作为美好的东西,首先就应该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使用,可见祭祀中酒的地位。饮酒行为是受到礼的制约的,中国古代酒礼是酒文化教育的核心,从酒行为去体现贵贱、尊卑、长幼等和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从酒文化的传统观念制止滥饮,提倡节饮,饮酒适度,即为提倡的饮酒之德。对酿酒销酒讲质量、重信誉等这些传统的酒礼和酒德,对名酒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酒作为美好的物质,在古今的历史长河中,表现英雄的豪爽气概,颂扬爱的真诚与纯洁,推崇和赞美智慧,引发文艺家创作激情。所有这些,说明酒与优美品格、美好感情、文化艺术互相增色,共同生辉。古代文人李白、杜甫、黄庭坚等对名酒的颂扬及提出的各种意见,对提高名酒声誉,促进名酒质量,都有强烈的激励作用。
(3)川茶
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首的茶叶,目前是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可缺少的饮料。世界种茶饮茶的发源地是中国,而四川是中国最早种茶、饮茶的地区之一。川茶是四川人民为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又一贡献。
川茶多特色。在唐代,蜀中有八大名茶,即“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锋,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扬村,绵州之善目,利州之罗村。”其中最负盛名的茶是蒙顶茶。“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这是白居易赞颂蒙顶茶的一句诗,有口皆碑,广为传诵。从唐朝开始蒙顶茶已作为贡茶,“蒙茸香叶如轻罗,自唐进贡入天府”。直至清朝,1000多年间,蒙顶茶年年皆为贡品,奉献皇室享用。
明代时,中国人饮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正如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供御茶》中说“……今人惟取出萌之精品者,汲泉置鼎,一淪便啜,遂开千古茗茶饮之宗。”而四川饮茶文化和出产茶种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明黄一正在《事物绀珠·茶类》中认为全国茗茶九十八种,而川茶占了二十一种,首推四川蒙山的山茶和雷鸣茶。
四川旧时茶馆最多,茶肆栉比,依山傍水。客来随意设座,泡茶一杯。碰上熟人,聊天,畅叙家常。四川人称之为“摆龙门阵”。或者背靠竹榻,遥望碧云蓝天,观赏山光水色,别有一番情趣。成都茶馆之所以受人喜爱,其原因就在于成都茶馆有茶、有座、有趣。所谓“有茶”,就是能让茶客得到满足。俗话说:茶好不如水好,水好不如器好。因此,成都茶馆的经营者在用水、备茶、置茶具上毫不含糊,颇具匠心。
沏茶之水,唐代陆羽《茶经》有言:泉水为上,河水次之,井水为下。成都无泉水,故一般茶馆都挂有上书“河水香茶”的招牌,以示招徕。一般茶馆都雇人用大木扁桶去取河心水,为此茶馆自然又得备几口沙缸以作过滤之用。
成都人喜欢茉莉花茶,但茶馆老板不乏生意经,为了满足南北往来的过路客,它们也备有其它各路名茶,把粉牌写得满闹热。有的考虑得更细致:夏天加备杭菊,解暑,明目;冬天加备沱茶,据说沱茶性温热,专供老年体虚者之需。
至于茶具,就是闻名遐迩的“盖碗儿”。这套由盖、碗、船组成的三件头茶具,可算把喝茶的艺术推到了臻于妙境的高度。最妙处在于茶船的定型和茶盖的巧思。据《资暇录》载,茶船为南齐蜀相崔宁之女所发明。有了它,既稳定了茶碗的重心,又免却了滚茶烫手之虞。茶盖最具巧思,有了它,茶碗不至于闭得太严,茶味得以徐徐沁出,能随意控制茶汁的溶解速度和茶水温度,还可避免喝茶时茶叶入口。
茶馆又是群众的“俱乐部”,最常见的是“打围鼓”(川剧坐唱),演唱者仅各执用一件乐器,如川锣、川胡、板鼓、大钹、马锣之类,很受百姓欢迎。有“围鼓”的茶馆,生意格外好。
旧时成都有句俗话,叫做“长官不如副官,掌柜不如堂倌。”的确,以应付茶客的功夫而论,成才的茶堂倌确实强于茶馆掌柜。堂倌雅称“茶博士”,源自唐朝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御史大夫李季卿宣尉江南,陆羽来见,衣野服,随茶具而入,手自烹茶,口通茶名,茶罢,李公命奴子取钱三十文,曰‘酬煮茶博士’”。看来这是古代文人间的雅谑,但“博士”之名由此传焉。堂倌的基本功叫“提壶掺水”。这是不可少的手上硬工夫:一把铜壶满水有十来斤,整天提在手,满堂穿花,在应对茶客的同时,还得卖点“手彩”:老远掺个“仙人过渡”;从茶客头上弄个险但又滴水不撒叫“雪花盖顶”;桌上的茶碗刚掺满,手上的茶碗又从水头上巧妙切入,来个“金蝉脱壳”;左右手各执一壶,同时掺一碗,叫做“二龙戏珠”;水满手不停,幺拇指轻轻一勾,茶盖子便稳稳地扣上碗口,名曰“海底捞月”等等。这一整套动作一环扣一环,一气呵成,若非久经锻炼是不行的。
四川茶馆既是休息娱乐场所,也是一种文化生活,在成都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增添了光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成都的城市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各类手工业产品贸易达于四方;城市建设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形成了内城、外城的格局;文化、生活习俗中的川剧、川菜、川酒、川茶也竞放光彩。明代的成都与汉唐时期的成都相比,在全国的地位虽然稍微有所下降,但作为四川经济文化中心、南北商业大都会的成都,仍然是全国几个重要城市之一,在西南、甚至整个南方都有重要的影响,在全国也是举足轻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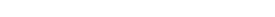
明蜀王陵博物馆 2015 版权所有 蜀ICP备1309412号 网站运营支持:万物智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