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蜀王府的营建和王府生活
1、蜀王府的营建
洪武三年(1370)七月,太祖诏建诸王府。四年(1371)正月,定亲王宫殿制度,王国宫垣内,左宗庙,右社稷。七年(1374),定亲王所居前殿名承运,中曰圜殿,后曰存心。四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明会要》卷七十二《方域二》。]洪武十八年(1385)太祖敕命四川布政使筹建蜀王府,成都府即在五代孟蜀后主宫城旧址的基础上建蜀王府,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89),蜀王府落成,[ 转引自程娟:《明朝历代蜀藩王》,见《成都文物》1996年第3期。]第一代明蜀王朱椿赴成都府坐镇。
蜀王府座落于四川成都府。成都府的历史沿革十分悠久,自禹贡时起已是梁州之地,属古蜀国。其地理位置优越,“上游水陆舟车通荆楚,下吴越达秦魏燕赵。真西南一大都会也。仪城十二里有奇,亦曰锦官城。内列藩封院司府县卫学校祠宇之属,外则含属州邑星棋布列,古所谓天府之国”。[ 明·天启(1621~1627)《成都府志》卷一。]虽处西南一隅,水陆交通却是便利。据嘉靖《四川通志·舆地志》所载,“大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言地利必资于形势也。蜀国为天府奥区,直坤维而躔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形势之险甲于寰宇。按其地东通荆楚,西接吐蕃,南界蛮荒,北连秦陇。其山崒嵂以嵯峨,其水甲渫而扬波。徼道千盘,严关四塞,雄藩巨镇拱卫。’”选此地营建蜀王府当为上上之选。与其他藩王府一样,蜀王府邸的选址运用了中国古代之堪舆学,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古代从春秋时期始就非常注重人与环境的关系。《管子·乘马》有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古人主张城市选址应考虑环境关系,注重将城市主体与周围环境统一经营。帝王的宫苑则大多利用自然山水改造而成,如桂林的明靖江王府建于独秀峰之下,四周众山拱卫,景色优美,确实是一个成功的选择。成都蜀王府的选址则为“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也。成都府也是一块风水宝地。其境内名山有岷山、峨嵋、青城、巫山,河流有峡江、雒江、涪江、嘉陵江、巴江、泸水、大渡河。而“巴城在岷江之北,汉水之南”,[ 清·常明:《四川通志》卷九《舆地志》。]可谓是“气”之所聚也。城内西北隅有山名武担,明蜀王府就建于武担山之阳。虽不象桂林独秀峰耸立于王府之中,也算得上是背有靠山。有“气”在,有靠山,古人认为如此一来,国祚必久矣!
据正德《四川志·藩封·蜀府》记载:“太祖高皇帝治定功成,乃封第十一子于蜀,建国成都。洪武十八年(1385)谕景川侯曹震等曰:‘蜀之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壮丽无以示威,汝往钦哉。’震等祗奉,营国五担山之阳,砖城周围五里,高三丈九尺。南为櫺星门,门之东有过门,南临金水河,为三桥九洞以度,桥之南设石兽、石表柱各二。红桥翼其两旁。萧墙设四门: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曰端礼,北曰广智。端礼在櫺星门之内,其前左右列顺门各二,直房各四。端礼门之内为承运门。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前为东西庑及顺门。承运门内为承运殿;前有左右庑;东西殿左右有东西府;东西偏(屋宇)为斋寝凉殿。后为圜殿。圜殿后有存心殿。又后为宫门,红墙四周,外左、右顺门相向。门内为正宫,鳞次五重。山川坛在萧墙内西南隅。其西为社稷坛,又西为旗 庙。承奉司在遵义门左。其他长史、仪卫司、典宝、典膳、纪善、典仪、良医、工正、奉祠、审理八所、广备仓库、左护卫俱错居萧墙外。”
宣德八年(1433)四月癸卯,工部奏:“蜀王言,王城损坏一百一十四丈,乞修理。”上命以成都护卫军为之。
此后又增修王府。嘉靖《四川总志·藩封·蜀府》载:“嘉靖二十年(1541),奏准包砌以石,设四门如砖城制。端礼门内为承运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前为左右庑及顺门。承运门内为承运殿,前为东西殿庑。左顺门入为东府,前为斋寝,右顺门入为西府,前为凉殿,俱向南。承运殿后为园,园后为存心殿,又后为王宫门,内为王寝正宫。端礼门前有水横带,甃月池为洞,铺平石其上。东西列直房。西南为山川社稷坛,又西为旗毒旗庙,东南隅为驾库。东有古菊井,驾路所经。端礼门前外东西道有过门,南临金水河,并设三桥,桥洞各三。桥之南设石狮、石表柱各二,其南平旷中设甬道,旁列民居、衙东西者四。正南建忠孝贤良坊,外设石屏,以便往来。更建坊于四衙,东南曰益懋厥德,东北曰永慎终誉,西南曰江汉朝宗,西北曰井参拱极。”萧墙内有菊井,为成都八景之一,曰“菊井秋香”。正德《四川志·成都府·山川》载:“菊井在蜀府萧墙内,即旧府学之前。”康熙《成都府志·山川》载:“菊井,蜀藩萧墙内,成都八景之一,名‘菊井秋香’。”雍正《四川通志·山水》载:“菊井在废蜀府萧墙内。”
万历末年,王府毁于火,旋即加以修复。《明史·五行志》载:“万历四十一年(1613)五月壬戌,蜀府灾,门殿为烬。”《明史·曹学佺传》:“万历末为四川右参政,按察使,蜀府毁于火,估修资七十万金,学佺以宗藩例却之。”
萧墙南垣在今东西御街一线,东垣在顺城街一线,北垣在羊市街、玉龙街一线,西垣在东城根街一线。经过几次修缮,王府的大体格局已定,规模宏大,足以慑“羌戎”。蜀王府主体为典型的早期亲王府格局,即三宫两殿。以端礼门——承运门——承运殿——圜殿——存心殿——王宫门——广智门为中轴,两边建筑对称排列,左宗庙,右社稷。在存心殿至承运门间,周迴有庑,同中心承运殿两边的庑构成“日”字形。按《明史》记载,早期的亲王府“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可谓气势辉宏。承运门台基用大青石块砌成,高四尺九寸五分,前后接以云阶、玉陛、石磴。正殿,即承运殿的殿基也全用平整的大青石块砌成,高六尺九寸,前后也接以云阶、玉陛、石磴。殿四周围以雕刻图案的石栏杆。殿顶盖青色琉璃瓦。廊房地高二尺五寸,王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后宫门地高三尺二寸五分(以上尺寸规格皆为洪武四年,即1371年所定)。经过洪武四年(1372)和十一年(1378)两次修订,最终确定亲王府城高二丈九尺,城周为三里二百四十三步三尺,墙基厚二丈,墙顶厚一丈六尺。
王府之外原有大城,年代早于明蜀王府。“洪武四年(1372)秋,傅友德等平蜀,令文忠往府(抚)循之。筑成都新城,发军戍诸郡要害乃还”。[ 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第8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后,都指挥赵清甃以砖石,见正德《四川志·城池》:“因宋元旧城而增修之,包砌砖石,基广二丈五尺,高三丈四尺。复修堤岸以为固。内江之水,环城而下。外江之水,环城北而东至濯锦桥南而合。辟五门,各有楼,楼皆五间。门外又筑月城,月城两旁辟门。复有楼一间,东西相向。城周回建敌楼一百二十五所。其西南角及东北角建二亭于上,俗传象龟之首尾。城东门龙泉路曰迎晖,南门双流路曰中和,西门郫路曰清远,北门新都路曰大安。其小西门曰延秋者,洪武二十九年(1396)塞之。宣德四年(1428)总兵官左都督陈怀讨松叠叛蛮,以成都根本之地,修城浚隍,至今赖之。”洪武二十二年(1389),永昌侯蓝玉“练兵,复督修城池”(《明史·蓝玉传》)。宣德三年(1428)陈怀又浚修一次,崇祯年间(1628~1644)刘汉儒复培修一次。此大城又称外城,成都蜀王府习称皇城,又称为内城。王府、萧墙和大城就形成了内、中、外三重城垣,似乎已固若金汤,无懈可击。
整个王府宅邸范围,包括今四川省展览馆及两边的成都市政府、原省工业厅、市体育中心、实验小学、二十四中一带区域。主体建筑坐北向南,四周绕以城垣。并设城门,且建城楼。城墙外围又置护城河。蜀王府城的外沿,南(前)面大致及今人民东路———人民西路一线;北(后)面达今之市体育中心及二十四中以北的东御河沿街———西御河沿街一线;东面接近今宾隆街———大有巷内侧往北一线;西面直抵平安桥———马道街外侧一线。恰好是座长宽皆约750米、占地约850亩的方城。护城河以外四面,还有广狭不等的附属区域。明蜀王府南城墙中段,设有横排并列的三道城门,此即王府正门。城门前方的护城河上,置建相应的三座石桥。再往前,则是一片旷坝,横阔与今天府广场相当,纵广比今天府广场还要大出一倍以上,南沿直抵今之红照壁街———新光华街一线。当时在这旷坝广场南端,正对王府城门及城楼,建有一堵巨型照墙,后世俗称“红照壁”。至若蜀府附续建立的十七系支宗,所传六十位郡王,则按朝廷藩制规定,皆不进住封地,而于本藩亲王建邸的府城或州城之内,以及该府州直辖的城郊地区(即所谓府、州的首县境域。比如当时成都府之首县,乃华阳县和成都县。华阳县辖成都东南半城及东南郊二十几乡;成都县辖成都西北半城及西北郊约近十乡)修建郡王府邸而居。关于蜀府郡王及所属支宗成员及至郡主之类,概不进住封地,而是尽皆建邸居于成都或四郊首县辖境。
2、蜀王府宗室的生活状况
由亲王衍生出了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及其他宗人,他们和亲王一起构成了整个蜀王府宗室。王府的最高统治者是出身于王室的亲王,宗室只能是王室的附庸,王的臣属。因此,宗室所受的待遇自然会有所降低。如官爵品级,亲王下天子一等,郡王下亲王一等,皆在正一品之上;镇国将军三品,辅国将军四品,奉国将军五品,以下逐级递减。而且宗室的爵位是代代下降的,直到不再有爵位,蜀亲王及郡王的地位则代代相因。再如俸禄,亲王岁支五万石禄米再加其它绫罗绸缎、食盐、茶、马匹草料,还有额外的赏赐;郡王岁支六千石禄米,其余和亲王相差不多,只是数量上有所减少。其他宗室成员的俸禄为: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洪武十二年,定王府禄米:将军自赐名受封日为始,县主仪宾自出阁成婚日为始,于附近州县秋粮内拨给。景泰七年又定郡王、将军以下禄米:出阁在前,受封在后,以受封日为始;受封在前,出阁在后,以出阁日为始。嘉靖四十四年,定宗藩条例:郡王、将军七分折钞;中尉六分折钞;郡、县主,郡、县、乡君,及仪宾八分折钞。[《明会要》卷四十三《职官十五》。]也就是说,宗室人员的岁禄支取方式一般为米钞兼支。除此外,郡王诸子年十五,人赐田六十顷,为永业。蜀王宗室的地位、待遇虽然比不上王室,但是与一般的同品级的内外文武官员相比却是较高的。如三品的镇国将军俸禄与正一品的内外文武官员相当,四品的辅国将军相当于正二品的官员等等。在礼仪上,王府将军的待遇也很高,按洪武二十九年(1396)十二月所定,“将军与驸马、仪宾、公侯相见,将军居左,驸马居右,皆再拜;与文武一品至三品相见,将军居中,各官拜,将军答拜;与四品以下官相见,各官拜,将军受。遇将军于道,驸马仪宾公侯让左并行,一品至三品引马侧立,四品以下下马。内廷出入由左门。凡传其言者称镇国将军裔旨,称呼之曰官人。”[ 漆招进:《靖江王府宗室》,见《桂林历史文化研究文集》,第231~256页,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永乐削爵后,藩王地位有所下降,特别是洪武年间拥有的军事权利,几乎全部被剥夺。而作为藩王部将的这些将军、中尉们,也就成了不带一兵一卒的空头司令。不过,尽管失去了兵权,其他方面的权利如食禄、礼遇等仍然保留。所以,即使没有了实际权利,却还在社会上受到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的尊敬。尤其是一些有贤德、有文采、性孝慈的宗人,更是受到蜀王的倚重。如万历二十年十月丁酉礼部言:“蜀王宣圻奏举德阳王府辅国中尉宣堣温良练达,汶川王府奉国将军承炎博雅孝友,俱堪协理宗学。随经四川抚按具题,宜如所请。”[《明实录类纂·宗藩贵戚卷》,第284页,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总的来说,整个蜀王宗室还算严守祖训,大部分都为贤良、好学、慈孝之辈,这自当得益于蜀献王朱椿的家训。
当然也有一些害群之马,如华阳王府。首位封爵的华阳王朱悦耀,是朱椿的庶二子,次妃金氏所生,“素敖不顺,为父所恶。一日,擅除所爱卒为千户,制冠带给之,献王闻知,大怒……杖之百余,将械之于朝”。此后,蜀世子悦谦未袭先卒,悦耀即萌生夺嫡之心,为父觉察,既逃往谷王橞处。朱椿薨后,悦耀又窃取府中银两并上奏朝廷对朱椿之嫡长孙加以诬陷,“意在去友堉,则王位以次及己”。仁宗即位后查明真相,于洪熙元年夏四月戊申,命悦耀迁居武岗州,赐书悦耀曰:“……湖广武岗州民淳俗厚,盖善地也。尔往居之,岁给尔禄米二千石,内一千石支本色,余折钞,其体朕惇睦之心,安意以行。”“仍赐纻丝罗各十五表里,白金二百两,钞一万贯。敕蜀王友堉,令遣人送华阳王家属赴武岗完聚,其平日随从之人悉还之,须厚资给,以尽事叔之道”。[《明实录类纂·宗藩贵戚卷》,第884页,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可见仁宗及蜀王并没有亏待华阳王,赏赐也算丰厚。但是,其子友土軍即位后仍不满足,认为保宁王悦劭虽为献王宫人所出,却能进袭蜀王爵位,享有封国之富,心中甚是不甘。于是上奏,“乞以献王所遗金帛器物、内使、宫女、官校分赐于臣”。及友土軍薨,蜀王“与银五百两付华阳王长子申鍷”。申鍷以数不足不受。宪宗十分不满,乃赐之敕曰:“先因尔父华阳王奏分蜀献王遗赀,已令蜀王量与银两,本无定数,既有五百两,亦为厚矣,岂可再索!敕至,即可领用,自宜安分守禄,图称藩辅之道,毋复妄意索求,有乖亲亲之谊。” (《宪宗实录》卷一 一九)华阳王不仅对蜀王室心有怨恨,而且对其宗人也甚为嫉恨,不加和睦。华阳王友土軍与弟镇国将军友壁互相讦奏。友壁奏其兄“尝率妃与宫人并军丁百余,出城围猎……及擅造钺斧金瓜等物、殿宇床座诸器,橬越龙凤日月,妄以宫女、玉带、绣衣赐童仆家人……累克军粮至二千余石”等罪。友土軍亦奏其弟“杖死军丁,擅受其妃父指挥夏瑄弓马”等罪(《英宗实录》卷二一二)。英宗遣人勘实,得知“友土軍容留僧弘川在府诵经坐禅,令老宫人事之;并逼军余办纳月钱银两,致逃走数多。友壁遇圣寿千秋等节,执私忿不赴府行礼,私奸家人,伐民间冢树,诬执平民为盗”。英宗特敕友琿:“王兄弟交恶以伤骨肉之情,惑于异端以招嫌疑之谤,急于财利以失天下之心,皆非保全名爵之道。自今以后,宜痛自改悔,循理守法。如或罔知改悔,仍蹈前愆,则祖宗之法具在,朕不敢私。”(《英宗实录》卷三三九)华阳王友琿甚至越制私造器物,据《英宗实录》卷二五二记载,景泰六年(1455)三月乙酉,“敕华阳王友琿曰:‘得千户买俊等首称蒙王差赉奏赴京,有内使魏祥传王令旨付银十两令买铜喇叭……大铜锣等器回,用凡百。该用器物,国有定制。逾制而妄用者,是于祖训有违。……于祖宗成训何如?……敕至,王宜循礼法,毋或仍前妄为,庶几永全令誉’”。虽然明皇一再的宽恕华阳王,但屡教不改、多行不义的华阳王最终还是被革爵。成化十五年(1479)闰十月辛未,华阳王申鍷与其弟镇国将军申铜由于“居丧无礼,弃母缺养,凶暴贪淫,戕害人命,所为不法,互相讦奏。遣锦衣卫百户杨纲会镇守巡抚等官勘实。命革爵,戴民巾闲住;申铜妻陈氏妒忌杀人,革其封号;及母妃杨氏亦多罪过,俱降敕切责;府中人违者坐罪有差”。被革爵后的申鍷并没有接受教训,“复强取妇女三人”,王“自言皆尝生子,并有娠者,不当遣”。宪宗遣人核实,“皆妄”。作为一府之首的华阳王不和睦宗室,更是不为宗人请名。弘治十三年(1500)五月乙丑,“蜀府庶人宾漉赴京奏乞赐封镇国将军职禄,上以无例不允,仍遣人送回,命华阳王严加约束”.
作为王室附庸的宗室有时也可改变命运,进封为亲王或郡王。如保宁王朱悦劭、罗江王朱有壎等以旁支进封为蜀王;江安王府至丘、东乡王府至沂由旁支袭封郡王。但是有机会晋升王室的毕竟是少数人,大部分宗人还是得安分守己地生活。不过,这些将军、中尉们的食禄如此丰厚、社会地位也高,只要量财度日,生活应该是很富裕、很滋润的。当然也有一些违法败纪、鱼肉百姓的败类,如华阳王府的友壁、申铜之流。这些坐享食禄的宗人们,随着明王朝的衰落也日渐窘迫。由于宗室的繁衍使得朝廷的俸禄支出越来越多,以致于入不敷出。再加上明末庞大的军饷开支,虽然朝廷三言五令要取消各王府宗室的俸禄,但实际上又无暇顾及,造成了万历以后“亲王或可自存,郡王以至中尉空乏尤甚,一旦盗起,无力御侮,徒手就戮,宗社为墟”[《明史·诸王世表一》。]的悲凉境地。
3、饮宴和礼乐
万历元年(1573)四月乙卯,蜀王宣圻奏定藩礼。礼部覆:“庆贺筵宴礼载在《会典》者,所当遵行,其出入承运门原不载《会典》,宜仍旧制,毋为纷更滋扰。”诏如议。
万历二年(1574)四月辛酉,礼部覆蜀王宣圻奏:“凡王国庆贺筵宴礼仪具载《祖训》、《会典》。今蜀王具奏至再,合行各衙门遵炤本部先次题奉钦依,悉加遵守。其出入承运门一节,《会典》查无关载,既经蜀王奏,系相传定制,相应一体遵守;其非《会典》所载及虽系旧规,而于典制无当者,该府不得越礼渎扰。”制曰可。
4、婚配制度
朱元璋众建屏藩之后,对王公贵族的婚配制度加以严格规定。可以说,明初诸王的婚姻成为了维系和巩固朱元璋军事集团的强有力的政治手段。为此还制定了选妃制度,如“选秀女”。明祖之制:“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有选秀女之”制。[ 陈江:《明藩王婚配制度考略》,《东南文化》1991年1期。]“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以皇孙及诸王世子、郡王年渐长,未婚,敕礼部于河南、北平、山东、山西、陕西,凡职官及军民家、或前朝故官家,女年十四以上、十七以下,有容德无疾而家法良者,令有司礼遣之,俾其父母亲送至京, 选立为妃;其不中者,赐道里费遣还。有司用是扰民者罪之。”[《明实录类纂·宗藩贵戚卷》,第642页,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既强调采于民间,又必须为“良家”之女,这是选王妃的重要原则。而且,明初尤其尚武:“中、东、西、南、北五城兵马指挥司:各指挥一人,正六品。副指挥四人,正七品。吏目一人。指挥巡捕盗贼,疏通街道,沟渠及囚犯。火禁之事……凡亲、郡王妃父无官者,亲王授兵马指挥,郡王授副指挥。不管事。”[ 陈江:《明藩王婚配制度考略》,《东南文化》1991年1期。]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也就只能出现此种现象:亲、郡王妃皆出身显赫,最差也是兵马副指挥使之女。蜀藩也不例外,见下表:
|
王 |
妃(次妃) |
妃父 |
妃父官职 |
|
靖王朱有堉 |
李氏 |
李昇 |
成都中护卫千户 |
|
和王朱悦劭火 |
继妃徐氏 |
徐讽 |
兵马指挥 |
|
定王朱有垓 |
蒯氏 |
蒯晋 |
西城兵马指挥 |
|
昭王朱宾瀚 |
刘氏 |
刘明 |
京师南城兵马指挥 |
|
成王朱让栩 |
何氏 |
何世昂 |
西城兵马 |
|
华阳王朱悦耀 |
徐氏 |
徐享 |
潞州卫指挥使 |
|
永川王朱悦烯 |
何氏 |
何瑄 |
中兵马指挥 |
|
内江王朱友墦 |
周氏 |
周容 |
南城兵马副指挥 |
|
石泉王朱友熕 |
马氏 |
马玘 |
西城兵马副指挥 |
|
汶川王朱友谵 |
蒋氏 |
蒋贤 |
南城兵马副指挥 |
|
庆符王朱友墂 |
李氏 |
李晔 |
北城兵马副指挥 |
|
南川王朱申锯 |
何氏 |
何辅 |
西城兵马副指挥 |
|
汶川王申销 |
杜氏 |
杜显 |
西城兵马副指挥 |
|
庆符王申镦 |
韩氏 |
韩海 |
南城兵马副指挥 |
|
华阳王朱宾沚 |
邹氏 |
邹贤 |
东城兵马副指挥 |
|
庆符王朱让檥 |
王氏 |
王升 |
兵马副指挥 |
|
德阳王承馨 |
林氏 |
林杰 |
成都左护卫指挥同知 |
|
汶川王承烔 |
杨氏 |
杨璔 |
兵马副指挥
|
而第一代分封的皇子更是与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们联姻,如第六子楚王朱桢配定远侯王弻之女;第十一子蜀王朱椿配以永昌侯蓝玉之女,第十三子代王朱桂则“妃中山王徐达女”。王弻、蓝玉、徐达之辈皆战功赫赫的武将,为朱元璋登上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并趁机笼络,以巩固朱明江山,朱元璋除了大封功臣外,还运用联姻手段,最终达到家天下之目的,可谓是用心良苦。当然也有封建思想中所谓的“门当户对”观念,以保证王族的纯正、优良血脉。此外,公主、郡主、郡君、县主、县君、乡主、乡君所配之仪宾也都出身豪族,其征选制度甚至比选亲、郡王的妃妾还要严格,择婿范围限于“官员军民”中豪族之“有家教者”,起码在明初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的公主、郡主“下嫁”。《明史·职官志》有载:“凡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并曰驸马都尉。其尚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者并曰仪宾。岁禄各有差,皆不得与政事”。王室婿称仪宾,取《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之义。
太祖之制:皇太子、皇子有二妃。纳次妃时,不传制,不发册,不亲迎。正副使行纳征礼,冠服拟唐、宋二品之制,仪仗视正妃稍减。[《明史》卷五十四《礼九》、《礼八》。]正妃之子为嫡子,如正妃无所出,王室可请封有所出的妾为继妃,“亲王生母准封继妃,郡王生母准封次妃,皆自其子之袭封者言之;其科妾媵有子,止得封夫人……请自后亲王之妾有子者,许称夫人;其子已袭封亲王而嫡妃不存者,许请封为次妃;郡王之妻,其子已袭封郡王而嫡妃不存者,许请封为夫人。仍请敕知会,不给诰命、冠服、及裁减身后祭葬。此外,毋得滥请”(《世宗实录》卷四Ο五)。各王府继妃只准封一人,但郡王不准封继。也就是说,明亲王有正妃、次妃(或继妃)、夫人、宫人等,郡王有妃、夫人、宫人等,镇国将军以下的元配皆称夫人。
从表面上看,似乎一朝踏入王室,从此便能光宗耀祖“一人得道,仙及鸡犬”,荣华富贵享用不尽,成为王亲国戚。因而各地的显门豪族争相攀龙附凤也是情有可原的。为了达到与王室联姻的目的,他们往往不择手段,使得秀女、仪宾的选征制度越来越形同虚设,走走过场而已。“宣德元年三月丁酉,上以旧制诸王子女婚娶皆由朝廷选授,比以宗室蕃盛,选之难悉得人,乃命诸王自今婚娶,或不及时者,悉自行选配,然后闻之朝廷,授以冠服册诰仪物。诸王便之”,[《明实录类纂·宗藩贵戚卷》,第666页,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有朝廷的默许,更加深了诸王婚配制度的黑暗。随着明皇朝的日益腐朽衰落,王室的婚配制度更加漏洞百出。王妃、次妃、夫人之位大部分为几个豪族把持,造成近亲繁殖的现象。以致于成化年间不得不颁布诏令,“禁诸王府不得以亲属为婚姻”。而仪宾也多为貌粗才浅之流。“景泰五年冬十月庚寅,礼部都给事中张轼等言:‘近年以来,各处王府选择仪宾赴京授职中间,多有人物鄙猥、相貌粗疏者。窃惟庶民子女尚因材求配,况国王乎?臣等风闻其故,盖因富豪子弟投托各王府主婚官员与议婚阴阳人通用作弊。有钱求嘱者,虽人物鄙猥,遂称年命相宜,堪与成婚。无钱求嘱者,虽人物聪俊,遂称年命相克,难以成婚。以此多不得人甚至有彼此相争赴京告讦者。”[《明实录类纂·宗藩贵戚卷》,第125~126页,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王室无法征选到有德有才之人,王室子弟的婚姻大事不能自主,也是身在王家的悲哀。当然这种悲哀也只是相对于郡主、郡君、县主等王家的女性后代和少部分亲王、郡王而言的。郡主、郡君们的婚姻大事当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纯粹是政治联姻的牺牲品。亲、郡王也只能接受主婚人士的安排,与“年命相宜”、“贤淑”之女成婚。相应的,一些亲、郡王们也就广置媵妾,甚至于“强取民间子女,又取娼为妾”。而明制对藩王“第一嫔”或“第一妾”之下“妾额”的数目也没有严格规定,促使以上现象更为泛滥。如荆王朱见潇“掠人妻女”,徽王朱载沦“夺民耿安女”,淮藩朱翊淇“与妓王爱狎,冒妾额入宫”等等。[ 陈江:《明藩王婚配制度考略》,《东南文化》1991年1期。。]相对于其他明藩的广纳媵妾,蜀藩就较为收敛,还未看到有关哪位蜀王“强取民女”的记载。明皇所谓的“蜀藩多贤王”应该也包括这一方面吧。
事实上嫁入王室也未必是福,“一入豪门深似海”。其间宫闱争斗之残酷,使得妃妾们整日整夜担惊受怕,以泪洗脸。一部宫闱史也就是一部妃妾们的血泪史。令人发指的是,明朝还有惨绝人寰的妃嫔生殉从葬制度。这是明藩王婚配制度中最落后,最野蛮又最隐秘的黑幕。如晋王府宁化郡王朱美壤薨于英宗遗诏禁殉之后仅七年,宪宗即追封其两名自经殉葬的宫人为“夫人”,足以证明英宗“罢宫妃殉葬”遗诏为一纸空文,对列藩南面称孤的小国之君无甚作用。蜀藩此类情况虽少,但也存在,如朱有堉薨,妃李氏、侍姬黄氏皆自经以殉。黄氏殉葬后,得以进封“夫人”。与殉葬制度相伴的是明朝的追封制度。当妃妾在宫闱争斗中落败后,选择死后追封成为唯一的出路。不仅王室妃妾如此难当,仪宾似乎也郁郁不得志。明制驸马、仪宾不但仕途阻绝,“皆不得与政事”,且“各藩郡县主,郡县君先仪宾没者,故事:仪宾得支半禄”。(《明史·诸王列传》)有更甚者或按“朝廷旧制:封杖责驸马二十下,减奉米八百石”,[ 陈江:《明藩王婚配制度考略》,《东南文化》1991年1期。。]既负丧妻之痛,又杖责减禄,其境可怜。
5、冠服制度
明洪武三年(1370)定制,册命亲王,先期告宗庙,所司陈设如册东宫仪。二十八年(1395)定制,亲王嫡长子,年十岁,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次嫡及庶子皆封郡王。凡王世子必以嫡长,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子止为郡王。待王与正妃年五十无嫡子,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袭封。朝廷遣人行册命之礼。册王妃与册太子妃仪同。[《明史》卷五十四《礼九》、《礼八》。]
对于诸王冠服,明朝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亲王冠服:助祭、谒庙、朝贺、受册、纳妃服衮冕(衮服和冕旒,衮服指古代君王等的礼服;冕旒指天子、诸侯等所戴的礼帽和礼帽前后的玉串),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服皮弁(古代男子戴的帽子)。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冕服俱如东宫,第冕旒用五采,玉圭长九寸二分五厘,青衣纁裳。永乐三年(1405)又定冕服、皮弁制,俱与东宫同,其常服亦与东宫同。
亲王妃冠服:受册、助祭、朝会服礼服。洪武三年(1370)定九四凤冠。永乐三年(1405)又定九翟(野鸡的羽毛)冠,制同皇妃。其大衫、霞帔、燕居佩服之饰,同东宫妃,第金事件减一,玉绶(绶带,一种彩色的丝带,用来系官印等,以表示身份)花、瑑(玉器上隆起的雕刻花纹)宝相花纹。
郡王冠服:永乐三年(1405)定,冕冠前后各七旒,每旒五采缫七就,贯三采玉珠七。圭长九寸。青衣(黑色的衣服)三章,粉(白色的)米在肩、藻、宗彝在两袖,皆织成。纁(浅红色)裳二章,织黼(古代礼服上绣的半黑半白的花纹)、黻(古代礼服上绣的半青半黑的花纹)各二。中单,领织黻文七,余与亲王世子同。皮弁(古代男子戴的帽子),前后各七缝,每缝缀三采玉七,余与亲王世子同。其圭佩、带绶、袜舄(鞋)如冕服内制。常服亦与亲王世子同。嘉靖七年(1528)定保和冠服,冠用七取,服与亲王世子同。
郡王妃冠服:永乐三年(1405)定,冠用七翟,与亲王世子妃同。其大衫,霞帔、燕居佩服之饰,俱同亲王妃,第绣云霞翟文,不用盘凤文。[ 张子模:《明代藩封及靖江王史料萃编》,第1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历代皇帝对蜀王的赏赐
历代明皇对诸王都有种种名目的赏赐,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新皇帝登基,对诸王加以赏赐
正统元年(1436)五月丁卯,遣内官赉送新编敕符簿于代,庆、宁、周、楚、鲁、蜀、肃、沈、辽、韩、唐、伊、郑、襄、荆、淮、梁、赵、秦、晋、靖江二十二王府各一扇,仍赐各王书,以易世纪元更属称换年号也。(《英宗实录》卷十八)
洪熙元年(1425)秋七月庚辰,赐诸王黄白金、文绮、錦、纱罗、布钞有差……晋、楚、鲁、肃、辽、韩、唐、伊、秦、蜀十王各白金三百两,文绮十表里,錦三匹,纱罗各十匹,兜罗錦三匹,西洋布五匹,钞二万贯。(《宣宗实录》卷三)
天顺八年(1464)二月戊戌,上以初即位,赐亲王白金文绮……代、蜀二世子各白金三百两、纻丝罗十表里、纱十匹、绵三匹、钞二万贯。(《宪宗实录》卷一二二)
(2)对诸王进贡的回赏
嘉靖三十九年(1560)五月丙寅朔,蜀世子宣圻进黄金一千两、白金一万两助的工。上嘉其忠悃,赐以金币,仍降敕褒谕之。(《世宗实录》卷四八四)嘉靖四十一年(1546)四月丙子,蜀王宣圻遣使进扇。赐白金三百两,文绮衣三袭。(《世宗实录》卷五O八)
历十九年(1591)蜀王捐银一千两助充军需。上诏褒奖之。(《神宗实录》卷二四一)
万历二十四年(1596)二月甲子,蜀王进扇,上命赐银一百两、大红罗衣一袭,仍写书复王。(《神宗实录》卷二九四)
万历二十八年(1600)七月壬辰,蜀王捐禄犒军。命写敕奖励,仍令抚按官备礼送府。(《神宗实录》卷三四九)
(3)赐名于诸王子女
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壬子,赐保宁王之子名曰友垓。(《宣宗实录》卷十一)
天顺元年(1457)秋七月丁丑,赐蜀世子嫡长子名申鈘……(《英宗实录》卷二八O)
(4)每年大庙或节日时诸王来朝,皇帝给予赏赐
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丁亥,蜀王椿还国,其从官侍卫赐予有差。(《太祖实录》卷二二五)
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丁酉,蜀王椿辞归……赐椿钞二万锭,其从官赐钞有差。(《太宗实录》卷十二下)
永乐二年(1404)二月丁丑,蜀世子悦燫辞归,赐钞二千锭。(《太宗实录》卷二十八)
永乐三年(1405)二月戊寅,蜀王椿辞归,宴如初至,赐赉甚厚,并赐其从官钞有差。(《太宗实录》卷三十九)
永乐三年(1405)冬十月丙寅,蜀世子悦燫辞归,上嘉其纯雅,论勉进学,赐白金、彩币加厚,其从官赐钞有差。(《太宗实录》卷四十七)
永乐十五年(1417)春正月丁未,……蜀王椿还国,赐蜀王银三千两,钞六万锭,米万石,各色纻丝五百匹,纱罗各二百五十匹,绢千匹,兜罗錦六十条,苏木五千斤,胡椒三千斤,马一百匹,鞍二副,火者百人。其从官赐钞有差。(《太宗实录》卷一八四)
(5)册封亲王及妃、世子及妃、郡王及妃时赐予金册或塗金银册及典宝等
宣德十年(1435)八月乙巳,赐晋王美圭妃孔氏、蜀王悦劭妃何氏金册……(《英宗实录》卷八)
万历四十六年(1618)七月丙申,周王肃溱、蜀王奉铨等奏讨典宝官及教授印信。从之。(《神宗实录》卷五七二)
(6)对有功的王加以奖赏
永乐十四年(1416)秋七月癸丑,赐书答蜀王椿曰:“去年谷府随侍都督张兴来言橞潜萌异图,言之至再,兄未之信。今得贤弟书,具有实事。人之无良,一至于此。贤弟以心,周公忠存王室之心也。仪宾顾瞻回,附黄金二百两,白金千两,钞四万锭,玉带一,金织衮龙纻丝纱罗衣九袭,纻丝线罗纱各五十匹,绒錦十匹,彩绢千匹,兜绵十条,高丽布百匹,米千石,胡椒千斤,马十匹,鞍二副,往致兄意,至可领也”。(《太宗实录》卷一七八)
(7)从诸王奏请给予特赏
成化二十一年(1485)六月癸巳,赐蜀王申凿《四书五经》、《续资治通鉴纲目》。从所请也。(《宪宗实录》卷二六七)
弘治八年(1495)四月癸亥,蜀王宾瀚奏:“先王薨后逾年,始赐封,未封前一年禄米乞并赐支”。给“户部议,不可。上命给与半年,不为例”。(《孝宗实录》卷九十九)
弘治九年(1496)十月壬辰,赐蜀王宾瀚四川提举司食盐岁三十引。从王请也。(《孝宗实录》卷一一八)
(8)其它
洪武十八年(1385)冬十月己丑,赐湘、潭、鲁、蜀四王十七史等书。(《太祖实录》卷一七六)
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戊子,以蜀王将之国,命户部运钞三十万锭赴蜀府,以备赏赉,并赐其从官军士一千八百四十人钞凡万二千七百余锭。(《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洪武三十五年(1402)秋七月乙巳,赐周、楚、齐、蜀、湘、代、肃、辽、庆、宁、岷、谷、韩、沈、安、唐、郢、伊、秦、晋、鲁、靖江二十一王各黄金百两、白金千两、彩币四十匹、錦十匹、纱罗各二十匹、钞五千锭。(《太宗实录》卷十下)
永乐四年(1406)九月辛巳,赐蜀王椿珍珠一百九十二两,白金一千五百两,钞二万锭。(《太宗实录》卷五十九)
永乐六年(1408)十一月癸酉,赐蜀王椿火者二十人,肃王英十人,庆王 五人。(《太宗实录》卷八十五)
永乐二十二年(1424)九月乙酉,赐唐王瑗烃、鲁王肇辉、晋王济熺、蜀世孙友堉、平阳王美圭各白金五百两、钞六千锭、纻丝二十表里、錦六匹、罗十匹、纱十匹。(《仁宗实录》卷二中)
正德三年(1508)冬十月丁丑,诏岁给蜀王世子让栩禄米三千石,俱支本色,不为例。时蜀王薨,世子奏禄米截日住支,家眷无以供赡,故有是命。(《武宗实录》卷四十三)
正德十二年(1517)十二月戊午,加蜀王食盐二十引,旧额已盈百引矣。(《武宗实录》卷一五六)
嘉靖四十五年(1550)十月丙子,蜀王宣圻辞常禄一千石,荆王翊钜辞常禄五百石。许之,仍各赐敕褒奖。(《世宗实录》卷五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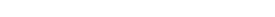
明蜀王陵博物馆 2015 版权所有 蜀ICP备1309412号 网站运营支持:万物智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