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蜀王陵 明蜀王室精美的地下宫殿
撰文/摄影 余茂智
成都东郊有处叫十陵的地方,地名的来源得于辖区内已经探明或者发掘的十座明蜀王陵墓葬。十座墓葬均分布于辖区的正觉山麓,由此而形成一处类似北京十三陵的王陵墓葬群胜迹,不由得唤起人们对它的一种别样暧昧情绪来。
在民间和古诗词中,墓葬往往为“黄泉”代名。“阳气动于黄泉之下,动养万物也”(班固《白虎通义》),“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可以说,几千年来,幽闭于地下的黄泉,既是众生的最终归宿,也是众生寄寓来世的一种载体。
那么对于不同于众生的皇家呢,明朝蜀王王室集体埋葬于此,正觉山麓的风水,到底为朱家皇室的魂灵提供了怎样的庇护?而是走进这些墓室,500多年后的今天,它们又将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出一派怎样的明代风貌?
青龙湖 明代蜀王打造的“风水宝地”?
正觉山是明代的古地名,今名大梁子。说是山,其实是一处山丘连绵的黄土陇岗。2011年的秋天,我和龙泉驿区博物馆的姚云书这里,但见坡岭起伏的山岗上,良田映秀,竹林疏布,不少农人正在地里忙着秋收秋种。村民们或许不知道,就在他们世代樵猎、耕种的土地上,竟然深埋着数以十座的明蜀藩王及其家族的王家陵墓。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年号洪武。一俟王朝建立,他便把自己的二十五个儿子除长子储于东宫外,其余全部分封各地建藩为王。首代蜀王蜀献王朱椿,是朱元璋的庶十一子,始封于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二十三年就藩成都府,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死后,子孙次第袭传王位。至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64年)八月,张献忠农民军攻破成都,十三代蜀王朱至澍偕妃妾投井自尽,蜀藩遂绝。
历代蜀王包括郡王都住在成都,他们死后也葬都在成都。据《四川通志》,第一代献王朱椿、第二代靖王朱友堉、献王之子悼庄王朱悦燫都葬在成都北郊的凤凰山,但因为一家两代四口均早夭无嗣,遂怀疑那里的风水有问题,于是从第三代蜀王僖王朱友壎起,蜀王皇室大多避西北而东南,将成都东郊选为他们的长眠之地,其中以大梁子、青龙埂一带最为集中。
根据考古发掘和探测,至今在这一地域方圆五公里的范围,已经发掘或者探明的就有僖王陵、怀王陵、惠王陵、昭王陵、成王陵、黔江悼怀王墓、僖王赵妃墓、僖王继妃墓、定王次妃墓、半边坟郡王墓等十座明代蜀王、蜀王妃、郡王及郡王妃的墓葬。
其实在过去,成都东郊的丘陵地带,在成都人的心目中都是一片荒郊野岭,是樵猎、墓葬之地。山间劳作的老农告诉说,就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梁子上的松柏连绵成片,浓荫蔽日,后来大炼钢铁,林木砍伐殆尽,这山岗才变成庄稼地的。不过,山岗之下正在建设的生态公园青龙湖正在着力恢复着大梁子过去的风光。透过铁丝网围栏,占地面积达一千五百的景区,林木葱茏,绿风浩浩,初步蓄水的湖面上,鹭鸟翻飞……
“这边是正觉山,对面凸起的山丘就是青龙埂。早在明代,这两处黄土陇岗合围着的就是有着千亩水面的古青龙湖。从已经探明的明蜀王陵来看,它们大多背山临湖,列布在这方圆五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姚云书的介绍,让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500年前的明代:古柏森森,波光粼粼,山岗朝霞染红山林,湖水涟漪轻荡绿风,风光无限。
但关于青龙湖,地方志上几乎没有记述。二十一纪初,因为青龙湖公园的建设,考古工作者曾经在离湖底不远的位置发掘出一座宋墓,可见,其时的青龙湖并非湖,不过有史料证实,最早的青龙湖成形于明代,后来因种种原因,至少在二三百年前就逐渐干涸而为零星水塘和湖溶田了。
我怀疑最早的青龙湖并非自然形成,因为从地势上看,湖的东南方是个明显的地理缺口,而据了解,即便今天重新围埂造湖,为了形成1500亩的水面,建设者也正在抓紧六处大坝的施工。如果不是,那么古青龙湖就是人造的了。那么是谁造的呢?而且谁才有这个能力实施如此浩大工程呢?或许就是明朝蜀王们的杰作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海拔534米的正觉山,是成都东郊最高的一座山丘,从中国古代人都十分信奉的风水学角度讲,这种高度正是所谓的“父母山”,系为靠山;而此山又以北高东西两冀渐低环抱之势,与西南面地势稍低的青龙埂和合,在南偏东方向形成“陵口”,从而使整个陵区“聚气凝神”。当北郊凤凰山的风水都有“问题”之后,明蜀王府的堪舆师们自然寻到这里,或许当年这里也并没有湖,于是便依着地势蓄水造起了湖,以此形成“藏风界水”之地。而事实上,从已经探明的各王陵的分布来看,它们均依势在湖的周围分布.形成指向湖心的掌状布局。
明朝的那些蜀王们相信,如此迎着东风、四至朝向俱佳的上风上水,一定能让他们的魂魄永结龙脉,永通王气。所以,数以十代的蜀王及其家眷,都最终选择这里作为他们灵魂“聚族而居”的栖息之地,也就不以为怪了。而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蜀王陵区的青龙湖再无人管理,最终导致这千亩古代名湖的逐渐干涸、消失,或许就是揭穿这个秘密的最合理的一种解释。
蜀僖王陵 早逝蜀王的黄泉世界和灵魂信仰
1979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大梁子山麓的石灵中学(已搬迁,今名十陵中学)扩建工程正在紧张的施工之中。当工人们往临时砌在学校西边土丘上的灰浆池里注水时,发现怎么也注不满,出于好奇,工人们挖穿池底,一个埋藏地下500多年的秘密这才从此展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这个秘密就是第三代明蜀王僖王朱友壎的王陵。和中国大多数王陵一样,僖王陵虽然也曾遭致盗墓贼的黑手,但整个地宫保存完好。盗墓贼窃取的无非金银财宝之类,至若各种冥器、陶俑和陶瓷器皿等,虽有扰乱和损毁,却大多留存。通过考古发掘,僖王陵共出土陶俑、陶马、陶家具、各类明器、《圹志》碑及水晶饰件等文物680件,为迄今为止蜀王陵发掘出土文物之最。
在姚云书的陪同下,我沿着僖王陵长长的墓道拾级而下。由于地宫深埋地下9米,站在由两块巨石凿成、布满乳钉的高大地宫大门前,一种盛气临人的压抑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及至进入地宫,那极尽奢侈的精致华丽,又让人在瞬间就迷离了眼。地宫呈三进三重殿四合院布局,分隔甬道庭室的四座门殿,为石结构四柱三开间仿木建筑,甬道、前庭和中庭的两边,都建有厢房,无论门殿还是厢房,均为琉璃瓦筒屋顶和龙纹勾头滴水,这些琉璃构件,都采用实用件四分之一的比例精良烧制而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门、窗、柱等,皆用石仿木雕,纹饰图案十分精美。地宫内的建筑,以前殿和正殿最高,其次是过庭和棺室,厢房最低,由此显示出建筑功能的主次之分,和有它带来的森严等级。
《大明蜀僖王圹志》石碑就立于进入墓室甬道的正中,它概括地记述了这位“王讳友壎”年轻蜀王的简短一生——朱友壎系首代蜀王献王之孙,二代蜀王靖王之弟。明宣德七年(1432年)九月袭封蜀王,因患风疾辞世于明宣德九年六月,享年26岁,在位不足两年。朱友壎去世后,大明王朝因其“淳厚端淑,言动率礼,未尝有过”,而按礼赐谥“僖”,所谓“僖”,“小心畏忌曰僖”,是为善谥。
在朱友壎时代,藩王的意义已大非于从前。要知道,明朝起初的藩王,不仅拥有多至数万的王府武装,而且还一定程度地拥有独断封地一切大小事务的权利。藩王权利的高度集中,一度影响到中央政权的威望和安危。直到明成祖朱棣上台,通过一系列削藩行动之后,那些世袭的藩王才成为并无实权,仅仅是身份显赫、尽享富贵的各地的王。而这个荣华富贵,也就更为贪婪地从地面延伸到了他们理想的黄泉世界了。加之僖王所在的明宣宗时代,正是明朝经济空前繁荣之际,手工业尤为发达,这从著名的宣德炉便可见一斑。而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上层社会奢靡之风更为盛行。
对比相关资料,精美的僖王陵地宫实则就是明蜀王府在地下的一个微缩,或者象征性的礼仪空间。姚云书告诉说,地宫发掘之初,甬道两旁有将军俑把守;前庭及两侧厢房,数百尊兵马仪仗俑及乐队吹鼓俑和执事俑,列队而立,气势庞大;中庭及两侧厢房,则陈列有椅柜几案、箱笼函匣、捧盒车轿等冥器模型,以及杯盘碗盏、壶瓶盆罐等陶瓷器皿,除此之外,兵弁侍卫、夫役仆从、僧道儒士、太监宫女、宫官执事陶俑,一应俱全。躺在石雕棺床上的墓主人,仿佛正安然地享受着他生前的富贵生活。
但绝非安享生前的荣华富贵这么简单,年轻的蜀王更加渴望的是,通过这个精心建造的如他生前家园般的黄泉世界,他的魄能够得到安息,他的魂能够升天。僖王陵的前庭、中庭均为青石拱券,只有棺室顶上施天花,全用石板横铺而成。其藻井为一轮藏传佛教中意为修成正果的八瓣莲花图案,每一瓣各刻宝伞、金鱼、宝瓶、莲花、法螺、吉祥结、宝幢、法轮等佛教八宝,莲心浮雕藏传佛教中象征寿命自在、心自在、愿自在等十相自在的梵文字母“朗久旺典”。
就其实而言,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把握上,明王朝总体是推崇儒家理学的。不过,朱元璋推翻的元代帝国却是以藏传佛教为国教的,所以,当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统治的需要,对藏传佛教实施的是“因俗以治”的安抚笼络政策,而明朝皇帝本身崇信藏传佛教的就不少,史料记载,明成祖朱棣就曾“征乌思藏僧作法会,为高帝、高后荐福”,及至僖王时候的明宣宗,也与明成祖一样,对藏传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不仅扶持藏传佛教寺庙瞿昙寺、大崇教寺的修建,还师从高僧班丹札失受闻密法。
当朝皇帝的宗教信仰,自然为整个皇室所效仿。所以,地宫里这位英年早逝的蜀王,当然也就渴望能在这种宗教礼仪的庇护下,升入天堂了。
王陵规制 蜀王功勋和贤明的嘉许?
与僖王陵隔青龙湖而望、西去1公里左右的香花寺大黄坟,是1958年兴修东风渠时,发现并经考古专家确认的一座明蜀藩王陵墓。今天略微隆起的这块偌大皇坟土坡遗址,实则是正在建设的青龙湖景区的苗圃基地,相传这里曾有庙宇名香花寺,皇坟便以此命名了。1995年,当考古工作者对皇坟地面建筑遗迹进行局部试发时,惊讶地发现其茔地总面积居然达87余亩(合明代100亩),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宏大的蜀王陵,不由得对墓主人进行了种种猜测。
依照《明史。礼志》的规定,即便是藩府亲王的寝园面积也不得超过50亩(约合今天的43.5亩),从已经发掘的僖王陵、昭王陵看,都无不符合这一规定,但香花寺大皇坟却超过一倍有余。要知道,依照明制,亲王陵寝都是“工部遣官造坟”的,但谁又敢违反定制无端扩大规模呢?在皇权专制的帝王时代,除非得到黄帝的特许与恩赐。那么在历代蜀王中,谁又最有可能得到如此皇恩浩荡的嘉许呢?
明史记述,首代蜀王朱椿,为人孝友慈祥,笃诚宽厚,性格与朱元璋众多儿子大不相同,不喜习武,尤爱博览群书,被朱元璋爱而戏呼他为“蜀秀才”。分封四川后,朱椿以礼教治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史称“蜀人由此安业,日益殷富”。但更为重要的是,朱椿在其四哥燕王朱棣举兵夺取皇位的活动中,自始至终,尽力声援;及至朱棣坐稳皇位转而削藩,遭到众多藩王抗拒之时,朱椿又率先垂范,主动削减王府武装,放弃干预地方政务和节制驻军的权利,而深受皇兄永乐黄帝朱棣的信任,恩赏有加。
清嘉庆《四川通志》明确记载了蜀献王陵在成都北郊的天隳山(今凤凰山),其子悼庄王朱悦燫在1972年的考古发掘中也证实埋葬于此。不过,作为郡王的悼庄王,其王陵地宫内空通进比僖王陵长6米,比昭王陵长12米,规模和规格显然不是一个郡王应该享有的。或许此墓本是朱椿预建的陵寝,不料儿子先去(朱悦燫明永乐七年去世,朱椿永乐二十一年去世),朱椿悲而怜之,求得皇兄特许,以己之墓葬之。加之皇兄感念他忠心耿耿,功勋卓著,哀其不幸,便敕令另行择地为其修建了超越规制的香花寺皇坟。
在姚云书的提醒下,我突然回想起僖王陵寝宫影壁上的那块蟠龙镂空陶雕——四角云纹围绕中,两条五爪金龙盘曲伸张,姿态十分优美。除此之外,不仅是僖王陵,包括2001年从成都锦江区潘家沟异地原貌迁建于明蜀王陵保护区的蜀定王(第五代蜀王,明天顺7年、公元1462年在位)次妃墓,其墓门上的乳钉也都是九纵九横计数81颗的。要知道,早在元代,龙纹的使用就完全被皇权垄断,并以法律形式予以明文规定。到明初,五爪龙纹只限于黄帝一人使用,分封各地的藩王也须遵其制,这种特权一直贯穿了明清两朝。至于大门乳钉,皇宫才能九纵九横排列,以此寓意九九归一,一统天下;而王府则为纵九横七排列,显示出严格的等级区分。
这些显然的违规越制,无疑只有得到皇帝的特许,才能建成。而这个特许,或许早在首代蜀王朱椿时代就破例了。作为一代贤王,朱椿自然深受朝廷的信任和喜爱,但他使当朝黄帝最为感动的,估计还在是朱棣初登皇位各方矛盾尚还十分激烈时,毅然告发自己母舅谷王橞和儿子朱悦燇的谋逆不轨,为此朱棣事后感叹:“王之举,周公安室王宗之心也。”朱椿的作为,为蜀藩王在皇室的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对其子孙产生深远影响,《明史》载,“蜀多贤王”, 明孝宗还专门下诏以蜀献王朱椿所定的家范作为整个明宗室的家法。
或许,正因为如此,蜀王一族,为历代当朝黄帝赞赏有嘉,其墓葬的规格也就因此而得到种种的破格提升。当然,这所有的谜团,都还有待于文史专家的进一步研究和考古发掘的证实。
谁荡平了明蜀王陵的地面陵园
考古人员在香花寺大皇坟和蜀昭王陵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中,除了地宫,王陵神道和享殿等地面陵园建筑的遗迹也有所发现。
龙泉驿区博物馆馆长姚云书认为,依照明代亲王陵都由“工部遣官造坟”的规定,明蜀王陵中的历代藩王陵,其建造规制和地面建筑格局都应该与同属明藩王陵的潞王陵和靖江王陵大同小异。地处河南新乡市的潞简王陵和地处广西桂林的靖江王陵,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好、最完整的明代藩王陵墓,从这两处王陵幸存的地面建筑看,都是以两侧仪仗队般排列着石人石兽的神道为中轴线,将陵园的陵门、前殿、享殿和墓地有序谨严地串接起来。
所谓神道,就是通往“魂魄、神灵”之道。在中国古代人们关于死亡的理论上,一个人死后,魄依附于死者的躯体留于“事死如事生”的墓穴之中,而魂则飞扬离去进入宿命中的理想世界。至于享殿,又称享堂、飨堂,内设死者的灵位,是死者亲属祭祀先人和守孝的地方。笔直的神道直通享殿和墓地,先庙祭祖先在天之魂,再扫墓祭祀祖先地下之灵,在中国古人的冥界概念中,自汉以后神道墓葬形式开始,死者幽秘的地下世界,便通过神道和享殿,实现了他与亲属的亲情交融,并与他生前的世界万世相通。
河南潞简王陵至今保存完整的王陵神道,一共肃穆对列有16对獬豸、石羊、石虎、狻猊、麒麟、骆驼、大象、石马,文武石人等,它们就像帝王生前的仪卫,忠心耿耿地守卫者主人的灵魂,并礼仪地迎送着四方来客。除此之外,潞简王陵还留存有石牌坊、神道碑、享殿等,姚云书认为,曾经的明蜀王陵园,也该有着相似的场景。至于那些藩府郡王,未袭亲王、郡王的王子、王孙以及王妃、夫人等的陵寝,则按制缩减规格和规模罢了。
事实上,考古人员在对香花寺大皇坟的试掘工作中,就曾发现其神道遗迹有180米之长,占地面积达87亩的整个陵园,以神道为中轴线由三个横长方形园子按墓向纵向排列连贯而成。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在陵园北侧的田土中,发现不少断残的石柱、额枋和石刻屋顶之类的牌坊构建。昭王陵因为毁损严重,有遗迹证实的其神道长度为寝园之外的50米,地面陵园和僖王陵一样,都大致为两个呈正方形的园子连贯而成。至于僖王陵的神道,因为推理所在的位置,早在发掘之前就已经是一条砖石混筑的乡村公路,故迹荡然。
虽有残留的遗迹可寻,但整个明蜀王陵地面陵园的集体湮灭,不仅让人猜想,到底谁是这些建筑销毁的罪魁祸首呢?要知道,在过去,帝王陵园都设有诸如“护陵监”之类的专门看护人员的,比如西汉长安的汉高祖长陵,惠帝的安陵,景帝的阳陵,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因为看护人员之多,一度的荒郊野岭甚至先后发展成了5个陵县。而在汉文化的传统价值观中,掘人祖坟无异于大逆人道,必将遭致天下人的谴责,即便是推翻了前朝的新皇帝,为了收买前朝遗民,巩固新政权,也大多会善待前朝的帝王之陵。就拿清朝皇帝来说吧,入关之后,不仅礼葬崇祯帝,还修整了明皇陵,同时按帝王陵园的规制,进行春秋祭祀,并定下祖训,清朝皇帝除了要祭祀十三陵,到了南京还必须祭祀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
谈及此,一段历史进入我们的视线。明末的四川,贪官污吏横行,民不聊生,曾经的天府之国,“乐土转为恶域”,在这种政治黑暗的历史背景下,草莽张献忠率六十万大军攻入四川,由于遭到地主武装的蜂起抵抗,张献忠采取了“除城尽剿”的政策,大开杀戒,甚至攻克成都之后,纵兵屠城三天。或许正是在这种杀红了眼的无理智疯狂中,为了斩断明蜀王室的龙脉,保证其称帝成都、仅存三年的大西政权昌盛永固,明蜀王陵的陵园悉数尽毁,从此荡然无存。
而这样的事情并非在中国政权轮替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史料记载,金灭北宋后,首先就是对北宋帝陵进行疯狂捣毁,除了劫财,更主要的是要破坏其风水以切断其帝业延续的基础。元朝兴起,金国灭亡后,元朝政府又组织起专业的盗掘陵墓机构,再次将北宋帝陵“尽犁为墟”。元灭南宋后,更是遍掘江南六陵,并在临安故宫筑起十三丈高的白塔,将所盗掘的宋帝尸骨填埋塔底,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帝王之魂,永世不得翻身。
僖王陵左侧的昭王陵,是在1991年考古发掘后,从龙泉驿区洪河镇白鹤村一组异地搬迁而来的一座夫妻合葬墓。进入复原的地宫,满目皆是断裂的巨石。现年70多岁的薛登老先生曾经参与过昭王陵的发掘工作,他说当初清理墓室时,发现墓主人的骨骸全都从拆散的棺椁里抛落在甬道和地宫之外;墓室随葬的各种琉璃俑、冥器等几乎全部砸碎,只有少量逃过浩劫;汉白玉镌刻的昭王圹志碑和碑座,被砸成碎块甚至齑粉;青石镌刻的王妃圹志碑则从碑座打到在地……情形惨不忍睹。根据墓室捣毁的年代和现状,考古人员初步得出结论,昭王陵如此悲惨的结局,应该为张献忠的部队所为。除此之外,与昭王陵相隔不远的白鹤村二组,有个叫“玉石碑”的地方,《华阳县志》记述地名的来历,说是张献忠部队捣毁明蜀惠王陵时,将墓内汉白玉的圹志碑弃之墓外,后来有人见其石质如玉,“即呼其地为玉石碑”。
好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还算短暂,否者,今天的我们或将无缘以睹僖王陵——这座号称中国最精美地下宫殿的精致华美,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它,而望见明朝蜀藩王府邸的富丽堂皇了。作为一种广集那个时代能工巧匠集体文化意识的礼仪美术杰作,另种角度讲,它是我们民族文化瑰丽的宝藏。
明蜀藩王黄泉路上的情感世界
异地搬迁于僖王陵旁的昭王陵,通过文物工作者精心复原,初现概貌大致与僖王陵的规模和布局相同。从墓门进入,依次为前庭、前殿和中庭。因为昭王陵是一座夫妻合葬墓,所不同的是,墓室中庭后部又分为左右正殿、后庭、后殿和棺室,左右棺室各设石质棺台一座。
从昭王陵那些残存建筑构件的浮雕纹饰,尤其是那块幸存完好的云纹双龙石碑可以看出,其艺术水准和凿刻工艺,比之僖王陵都要精致得多。看完僖王陵,再入昭王陵,你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僖王陵好似一座完好的清水房,而昭王陵则是破损了的精装房。
明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崇尚节俭,其祖训曾对一切营建提出要求,“但求安固,不事华丽,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并要求“后世子孙,守以为法。”僖王朱友壎去世,距离明朝立国66年,距离太祖朱元璋去世36年,此时的明朝虽已经步入正统,但太祖训示依然如雷贯耳。而昭王朱宾瀚去世距离明朝立国已有140年,此时正值明朝中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上流社会奢侈之风盛行,这从墓室的精美度便可见一斑。
昭王陵残存的圹志碑文告诉我们,八代蜀王昭王朱宾瀚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辞世,享年28岁,在蜀王位14年。与其合葬的王妃刘氏,系当时治所成都的宁川卫一个将军的女儿,“以贤淑择配王”后,与朱宾瀚育有一子,“曰让栩”,就是明正德五年袭封蜀王的九代蜀王成王朱让栩。正德十三年,刘氏因病去世后,由“布政司委官开圹合葬”昭王陵。其实,从昭王陵的建筑结构来看,在造墓之初,无疑就事先作好了将来夫妻同葬的打算。
在中国古代人的夫妻观念和冥界观念中,一旦结合为夫妻,无论阳世阴间,都永不分离。《诗经。王风。大车》中有“毂则异室,死则同穴”的诗句,意思是今世不能配对成双,死后也要共坟同穴;《唐风。葛生》相关的诗歌也有收录,“夏至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穴。”这是一首哀叹丈夫出征一去不返的歌谣,诗中的“居”、“穴”都指坟墓,全句释为,漫漫的夏日冬夜,格外思念远征的丈夫,希望死后能与夫君埋葬一起。
而这个夫妻同穴的墓葬观,与战国到西汉时期,竖穴墓葬向洞室墓葬的转变有着巨大的关联。从礼器相随的封闭地下空间,转为随葬生活日用品、与死者生前故居相仿的洞室,人们日益相信,冥冥中的黄泉,是人们死后生前的延续和再现,今世夫妻在在黄泉路上依然是夫妻。从考古发掘中,各地历代夫妻合葬墓都时有发现。但帝王们或许不愿意如此,因为他们渴望在死后依然拥有三宫六院,妻妾成群,与谁合葬都不合适。当然也有特例,比如唐乾陵,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与其夫唐高宗李治的合葬地,也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夫妻合葬帝王陵。
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的核心与基石,“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夫和妇柔,恩爱相亲,和睦的家庭关系必然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和政权的稳定。但朱熹的理学,直到明王朝的建立,才成为皇朝政权正统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明王朝对朱熹理学可谓推崇备至,要知道,明朝时期的科举考试,要求所有题目都须出自朱熹编订的《四书》。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背景,明王朝的王陵制度规定,继妃、次妃、妇人死后,一律“造圹祔葬”,之后又再次重申,“继妃则祔葬其(本王之陵)旁”。所谓“祔葬” 即合葬,或者葬于本王陵园本王坟茔之旁。所以,从相距僖王陵数百米之遥的僖王赵妃墓、僖王继妃墓来看,它们皆符合这一定制,从中反映出明王朝对王室家庭关系的重视。
再说昭王陵,其最为奇妙之处在于两个棺室隔墙上一孔镂空的门扉,据说这是为了方便夫妻两人在阴间的联系。这样的设计,无疑反映出夫妻二人生前的和睦恩爱。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王室家庭的和谐美满,才培养出了一代贤明蜀王朱让栩,史料记载,除献王朱椿外,九代蜀王成王朱让栩也贤明有为,“让栩尤贤明,喜儒雅,不迩声伎,创义学,修水利,振灾恤荒……”,不仅深得川中百姓的爱戴,明世宗嘉靖黄帝还对他进行了特别的嘉奖,赐建 “忠孝贤良”牌坊,以示表彰。所以学界也有倾向于超越规制的香花寺大皇坟,为嘉靖黄帝嘉许的蜀成王陵寝之说,而且,考古人员在试掘中通过初步发现的龙纹滴水和凤纹滴水判断,香花寺大皇坟也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明蜀王府太监们的最终归宿
2003年,成都相继发掘出土了两处规模庞大的明代太监墓葬群,引起文物考古界的轰动。两处墓葬群一处地处城北的五块石,一处地处城南的红牌楼,它们均按墓葬年代互为比邻,一字排开,所不同的是,红牌楼9座明朝弘治到万历年间的太监墓为坐西向东向,而五块石多属明嘉靖年间的11座太监墓都坐北朝南向。之后的2005年,考古人员又在城南的琉璃场发掘出土了明万历年间的7座一字排开坐西朝东向太监墓。这些太监墓的建筑形制都大体相同,均为券顶长方形,由封门石、外八字墙、前室、后室以及壁龛组成,可见它们都是同一规划而建的。
太监,也称宦官,在中国古代,他们是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中国的太监史长达3000年之久,不过,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太监并非全是阉人,直到东汉时期,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皇族以为如果允许男侍出入,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太监这才全部为阉人担当。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阉割事件,发生在太平天国时期,史料记载,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不久,就一次阉割十岁以下男童达六七百人,存活者仅“十之二三”,分给东王、天王、翼王等。
曾经的明蜀王府到底有多少太监,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不过,这些太监死后,大都被埋葬在成都东南郊和西北郊地势较高的寺庙附近。比如城东南南的桂溪寺、祝国寺,城西北的慈云寺等地,都曾发现过规模不小的太监墓群。这些太监墓群都是以城中的蜀王府为中心,呈拱卫之势分布城郊,借此来表达对主子的忠心,也暗含着死后继续守卫服侍主子的意思。
比之历代,明朝太监的权势十分强大,这个源头在于明成祖朱棣,这位依靠太监夺位的皇帝,不仅设立专门的学校,让太监读书学习,还让太监帮忙处理朝廷的日常工作。到明熹宗时,大太监魏忠贤更是把干预朝政的权势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拥有生杀大权,以至不少朝中官员都惹不起这些太监,就连大学士杨升庵也曾为太监写过墓志铭。
但蜀王府的太监到底权势如何呢?1972年,成都西郊出土了一座太监墓,根据墓志铭,墓主人腾英是当时蜀王府的“藩门”副职,官至五品,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任为朝廷命官“内局典司织造”,负责宫内所需蜀锦的营造。除此之外,不能传宗接代的腾英,还收有养子,俨然拥有正常的家庭。
一个藩王府的太监,升任为朝廷命官,可见那个时代太监的社会地位,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明代太监墓葬的华美。而事实上,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即便是那些藩王府的太监墓,也都为大型石室墓,分前室后室建造,八字墙上的蟠龙浮雕,凿刻精美,仿木雕刻的石质墓门精致有家,墓室石壁上等壁画,有的还饰以金粉,且金饰、银器、玛瑙、玉器等奢华随葬品均有数量不少的出土。
2004年,成都红牌楼、五块石出土的明代蜀王府太监墓葬群,被集体搬迁到地处十陵镇的明蜀王陵区,在四五百年后重见天日的今天,继续“效忠”和“侍奉”他们的蜀王及其王室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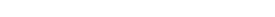
明蜀王陵博物馆 2015 版权所有 蜀ICP备1309412号 网站运营支持:万物智汇